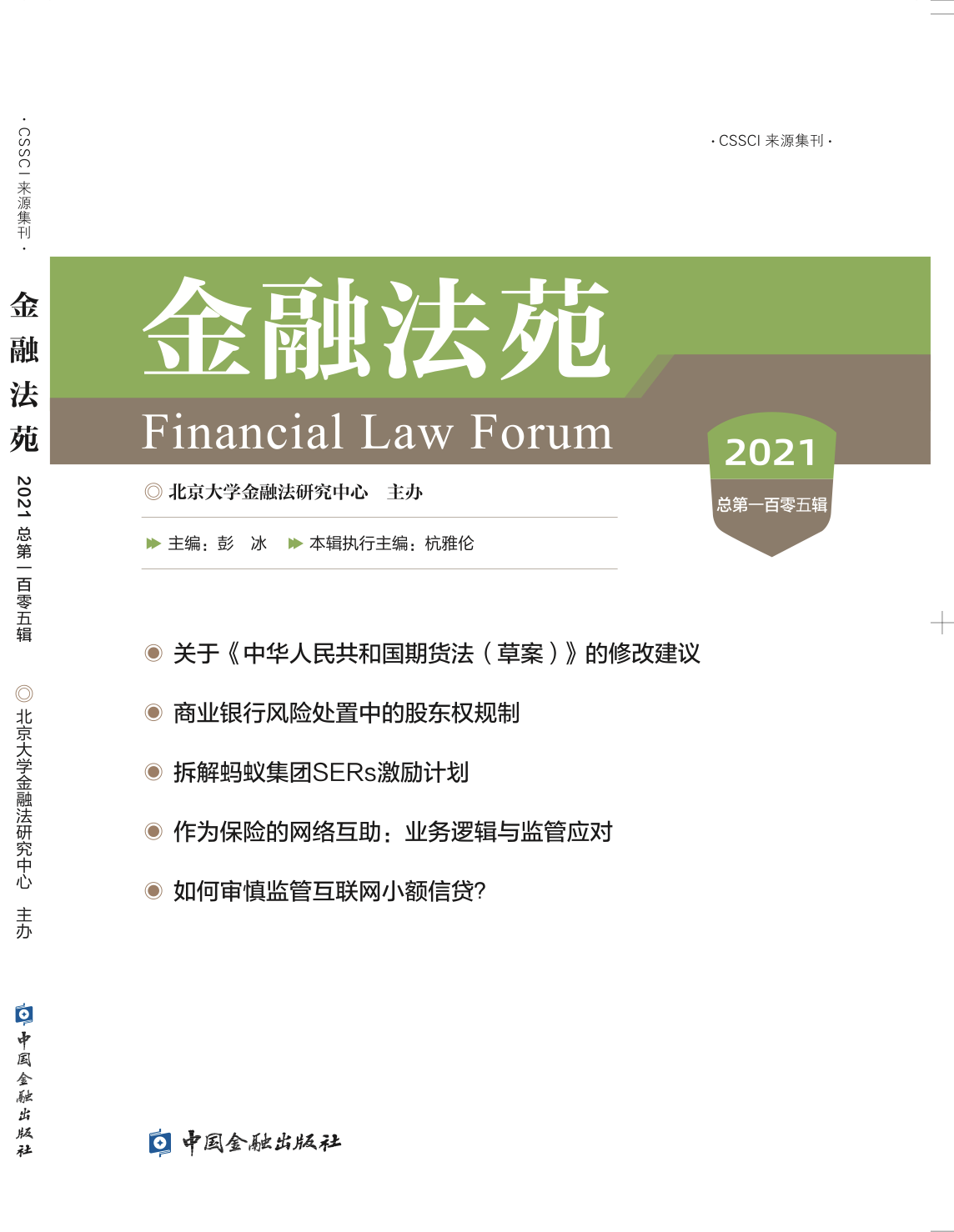案情:
1992年8月15日,何某(以下简称“A”)在建行某市分行一储蓄所(以下简称“储蓄所”)存入人民币3万元(为记名整存整取一年期储蓄存款)。1993年A因交通事故去世,该笔存款的存折下落不明。次日,A的父亲B委托亲戚C前往储蓄所办理该笔存款的挂失止付手续。C在《挂失申请书》上写明挂失原因系车祸丢失存折,并提供C本人的身份证。该储蓄所向C收取了挂失的手续费,在《挂失申请书》上加盖了业务章,并出具了《挂失申请书》第三联单给C。1993年2月2日,建行市分行审查认为,该笔挂失“缺乏储户本人身份证,违反银行挂失原则,挂失无效,请立即予以撤销”,并向储蓄所发出内部通知。1993年2月4日,储蓄所撤销该挂失申请,但没能及时通知B与C。 1993年8月16日(即存款期限满后第二天),储蓄所凭取款人所持的存折支付了该笔存款的本息(合计人民币32, 443.12元)。1993年10月,B委托C持《挂失申请书》向储蓄所要求支付该笔存款的本息。该储蓄所告知应提供继承公证书等有关文件。1993年11月,当B持继承A存款的继承公证书等证件再次向储蓄所要求取款时,储蓄所才将存款已被他人领走的率实告知B。此后,经双方多次协商,储蓄所均拒绝支付存款本息,为此,13向区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建行市分行支付该款的本息,并承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被告辩称,原告的挂失申请缺乏储户本人身份证明,违反挂失原则,为无效挂失,撤销“挂失”是合法的。此后被告凭存折支付了该笔存款本息也是合法有效的。故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两审法院裁决及其理由:
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储户A因存款与被告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其死亡后依法应由其唯一合法继承人原告B继承。被告负有按存款合同约定妥善保管存款和凭存折予以支付的义务。在存折遗失以后,存款没有被领取以前,原告即向被告的储蓄所提出书面挂失申请。被告在原告方未能提供齐全的储户本人身份证明的情况下,仍出具《挂失申请书》给原告,并且收取挂失手续费,应视为原告的挂失申请已经得到被告的认可并成立生效。事后被告经审查以不符合挂失原则为由,单方面内部撤销该挂失,是无效的。在原告挂失申请仍有效的前提下,存折的持有人已不是该笔存款的合法持有人。原存折也不能再作为被告履行支付义务的凭据。而被告仍仅凭第三人所持有的存折就将该笔存款本息支付给第三者,其过错是明显的,故被告的清偿是无效清偿,效力不及于原告,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故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于1994年10月12日判决:被告应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该笔存款本息32,443.12元。
一审判决以后,被告不服,以“原告取得挂失申请书并不意味着挂失申请已经得到最终确定,该挂失申请不符合银行有关规定,予以撤销是合法有效的行为”为由,向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在二审期间,上诉人主动提出调解。经法院主持,双方于1995年1月23日达成如下协议:
上诉人赔偿给被上诉人人民币3万元;被上诉人自愿放弃对该款利息部分的赔偿请求权(资料来源:刘家琛主编《金融案例选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评析:
本案争议所涉及的合同(契约)是非常普通的一种,即储蓄合同。其普通性可能仅次于买卖与民间借贷。中国数万亿元存款就是通过该种合同的签定、履行实现的。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性,致使人们忽略了对它的分析,从而当因出现变故需要重新安排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时,往往出现纠纷。本案就是一例。本案的主要焦点是存折挂失是否有效。在认识挂失有效性的前提下,再来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争议是合同之债,还是侵权之债。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存折“挂失”的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1993年1月12日发布并实施的《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37条规定,存折如有遗失,必须立即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并提供有关情况,书面向原储蓄机构正式声明挂失止付。储蓄机构在确认该笔存款未被支取的前提下,方可受理挂失手续。挂失七天后,储户需与储蓄机构约定时间,办理补领新存单(折)或支取存款手续。因此,根据该《若干规定》的规定,“挂失”既是要式的、又是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挂失”应当履行特定的方式,“挂失”应当通过双方的共同作为来完成。
本案中,A因交通事故去世后,A的父亲B委托亲戚C以C自己的身份证到银行挂失存折,这是不符合《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的。但被告的储蓄所仍向C签发了《挂失申请书》。据此,储蓄所签发《挂失申请书》的行为本身说明储蓄所确认A已经死亡的事实,并认可了C的代理行为。在储蓄所与存款人之间的储蓄合同内容也就发生了变更,即银行不能再凭“存折”支付存折上约定的款项。也就是说,挂失行为已导致合同变更,“挂失”成为合同的一部分,“挂失”与原储蓄合同共同组成了新的合同。
当然,前述新的合同并非是完善的,因为B及B的代理人C没有在挂失7天后,与储蓄所约定时间,办理补领新存单(折)或支取存款的手续。对于这种情况的法律后果,《储蓄管理条例》与《若干规定》皆没有相应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一点不是合同的根本内容,不影响新合同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而只是有关合同的履行方式问题,并不足以导致“原告的存款被他人提取是合法的事实”。
被告在随后的内部审查当中,发现储蓄所的做法不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认为“挂失”无效,要求撤销。笔者认为,被告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民事行为是否有效,不依赖于当事人的主观看法,而是取决干法律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很明显,本案的“挂失”行为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挂失”自然也就无“无效”可言。
当然,本案的“挂失”不符合部门规章的规定,但被告的储蓄所既然予以确认,就应当认为是有效的。被告发现“挂失”不符合条件的问题以后,应当告知B或B的委托人c前来办理变更手续,而不能单方面撤销“挂失”,因为撤销“挂失”将导致合同的“再”变更,应当告知存款人,否则撤销“挂失”的行为无效。
我们知道,在民事合同的签定、履行与变更过程当中,民事行为的发生是有先后的。这些民事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合同的签订、履行或变更,比如要约、承诺、交付款项、签发存单等等。当在先民事行为存在瑕疵,而对方当事人知道而没有抗辩,却予以确认,并随后为民事行为,从而构成民事合同的签定、履行或变更时,给予确认的当事人在合同以后的履行过程中,不得基于前述民事行为的瑕疵进行抗辩。
因此,被告要想撤销挂失,必须同原告共同完成。同时,这也是债权的相对性决定的。债权是对人权、相对权,即权利主体只能向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主张权利。因此形成“债”的合同的签定、变更、解除与履行不能单方面完成。
无论是前述民事行为瑕疵的抗辩原理,还是债的相对性原理皆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信原则的体现。原告的代理人办完“挂失”以后,基于对储蓄所的信赖,必然确信储蓄所不会再凭“存折”支付存款的本息。毫无疑问,储蓄所应当本着B对储蓄所的这种信赖行事。这也正是“挂失”的法律意义所在,也是“道德是法律支点”的体现。因此,在本案中,被告认为“挂失”已经撤销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储蓄所应当向原告支付全部存款与利息(利息还应当包括迟延支付期间的利息)。
二、是侵权之债,还是合同之债?
就本案看来,原告B是A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因此原被告之间是储蓄合同关系无疑。被告储蓄所到期向案外人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不向原告支付存款的本息,是被告储蓄所合同履行上的对象错误,原告的债权并没有得到实现。由此可见,原被告基于储蓄合同产生的纠纷是“合同之债”,而非“侵权之债”。因此被告承担的主要责任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而是违约责任。
我们知道,“债”是债权、债务或债权债务关系的简称。是称为“债权”、“债务”,还是称为“债权债务关系”,主要取决于“称谓”的侧重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四种“债”,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就合同之债来说,根据《民法通则》第111条的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约定,即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要求赔偿损失。就本案的储蓄合同纠纷看,无论是“本金”、还是“利息”皆无条件地属于存款人的继承人B。也就是说储蓄所向原告支付3万元的本金及其利息,是储蓄所储蓄合同上的义务。支付本金与利息仅仅是储蓄所在履行合同。
由于储蓄所义务的载体是货币的支付,因此对于本案而言也就不存在“合同履行不能”的问题,自然也无“相应的补救措施”可言。而如果说有“赔偿”的话,则还应当包括存款“到期日”至“被告实际履行法院裁决之日”期间的利息。对于这一部分,笔者认为原告存在愿意放弃的可能性,因为原告有“说法”对被告储蓄所不支付“存款本金利息”给予谅解。而原告“放弃”存款本金的“法定孳息”—一年期存款的利息—似乎就变得不可理解了,因为原告是经过一年多的周折方仅仅部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且就本案的整个审理过程可以看出,一、二审法院、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就被告储蓄所拒绝支付存款以后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存款到期日至法院裁决执行日的利息—作出反应。笔者认为这主要在于原告没有认识到储蓄所全面、及时、准确履行合同是储蓄所合同上的义务,是自己合同上的权利。而法院则是对原告这种权利意识的淡化予以漠视,因为一、二审法院的裁决皆没有提及利息赔偿问题,而是将储蓄所履行合同上的义务视为对原告的赔偿。这实际正是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难题之一:与淡化权利的意识作斗争。因为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为权利而斗争既是市场主体对自己的义务,也是市场主体对社会的义务,否则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不会在中国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是合同之债,而非侵权之债。该合同之债存在三个债的关系:一、3万元的货币(本金)之债;二、2,443.12元的利息之债;三、存款到期日至被告履行法院裁决之日的利息赔偿之债。因此,原告的主要主张不应当是赔偿损失之诉,而是请求被告实际履行合同之诉。被告对第三者履行合同虽然对于被告自己而言是一种损失,但从法律上讲,对于原告与储蓄所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不产生任何影响。由此来看,一、二审法院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原告的主张,但有关概念显属使用不当。这也就决定了法院不可能彻底保护原告的主张。或许这正是本案得以调解结案的内在原因。同时,笔者很对原告的自愿性表示怀疑,这也是本案调解结案可供圈点之处。
本案的出现也许与我们金融制度的传统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谈不上什么民事合同与民事活动。而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银行大多是国家机关,银行的存贷款行为也不是商行为,自然也就缺乏契约的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纽带,金融机构也主要是通过契约建立与社会各界的关系的,因此银行应当多一些契约上的概念,多一些法律意识。否则,银行对自己义务的淡化也就是对他人权利的忽视,从而给契约相对人带来权利实现上的障碍,同时也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3万元对于一个储蓄所来讲也许完全可以承受得了,但如果是30万、300万、3000万、3亿、30亿、300亿怎么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例,我们应当从本案中汲取一些东西。

1998 > 1998年总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