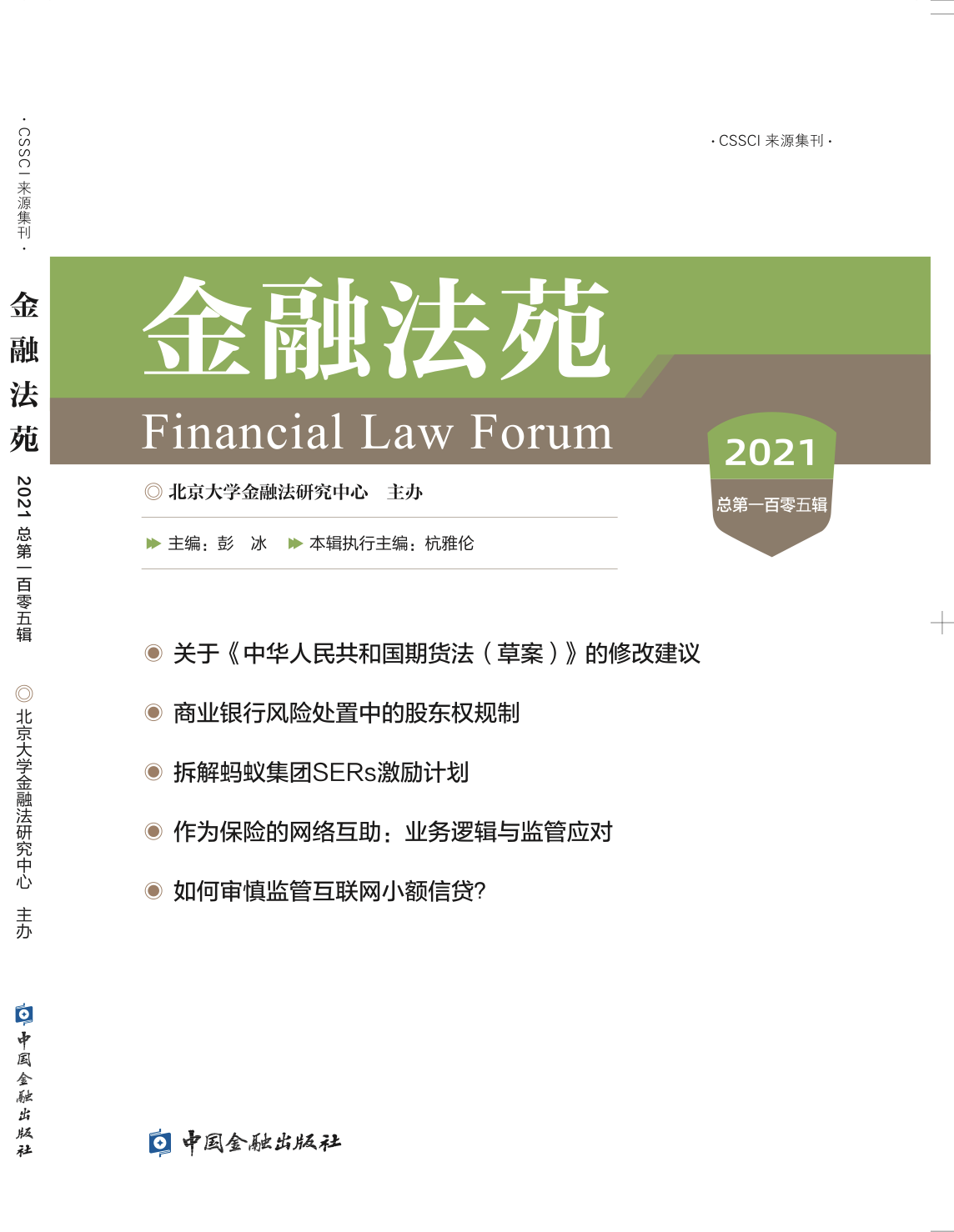四、类别权利的变更(Variation )
当类别权利得以确定之后,什么情形、何种行为构成对既定类别权利的变更?回答此问题的意义在于确定《1985年公司法》第125条的适用,即当附于某些股份之上的权利被认定为进行了“变更”或“废除”时,需要持有3/4以上这些股份的股东的同意或持有这些股份的股东单独召开股东大会批准。
部分对类别权利的变更是比较容易认定且争议不大的,如直接废除类别权利、注销类别股份、减少优先股股息的比例等。但在某些情形下,公司提出的议案是否构成对类别权利的变更,则存在颇多争议。英国判例法有大量的案例尝试在不同的情形下对这一问题给予回答,但其给出的答案中显然否定远远多于肯定。
(一)按比例减资不构成变更:Mackenzie&Co.案[1]
Re Mackenzie&Co.,limited案判决于1916年,案情如下:
Mackenzie公司成立于1900年10月2日,经营葡萄酒和烈酒。资本为200000英镑,分成10000股,每股面值20英镑,其中,6000股为4%累积优先股,4000股为普通股。已发行资本包括5300股优先股和1578股普通股,股款均已付清,其余700股优先股和2422股普通股尚未发行。
自从1912年以来,优先股股息均按惯例支付,但普通股未获得任何股息。在1915年对公司资产进行的评估中,发现公司亏损34390英镑,相当于已发行股本每股亏损5英镑。
1915年9月15日,公司向所有股东发出通函,通知定于1915年10月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随附提交审议的减资方案:由于亏损情况的存在,提议每股面值减少5英镑;并且,鉴于葡萄酒生意的萧条状态,公司只需要20634英镑以上的资本,因此,提议通过向每个股东返还3英镑,进一步减资。股东通函中写道:“必须获得法院的批准。根据章程,优先股股东无权在临时股东大会上投票,但是董事愿意听取您同意该计划的意见。”作为回复,1947股优先股股东同意该计划,2210股优先股股东反对该计划,1143股优先股股东保持中立。
1915年10月8日和1915年11月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在两次股东大会上,普通股一致通过特别决议,批准:(1)注销未发行的700股优先股和2422股普通股;(2)注销已亏损或不能代表现有资产的资本,即5300股优先股和1578股普通股每股面值减少5英镑;(3)返还5300股优先股和1578股普通股的持有人每股3英镑。其结果为,将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00英镑减至82536英镑,其中5300股为面值12英镑的4%累积优先股,1578股为面值12英镑的普通股。
优先股股东没有出席或被代表出席第一个股东大会,但是股东大会在提交议案时宣读了以反对该计划的优先股股东名义发出的信函。反对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优先股的特别权利将因此发生变更,但却没有根据公司章程第64条得到持有已发行优先股2/3的股东的书面批准。第二个股东大会的通知没有送给优先股股东,优先股股东也没有出席或被代表出席第二个股东大会。
1916年2月28日,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确认减资方案。在听证会上,1947股优先股支持该申请,但1889股优先股,即超过已发行优先股1/3的持有人反对该申请。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包括:
第5条:“公司资本为200000英镑,分为10000股,每股面值20英镑,其中6000股为4%累积优先股,4000股为普通股,其各自的权利和特权在本章程中予以规定。”
第6条:“除非本章程对类别股份的创设有相反规定,附于任何类别股份之上的特殊权利、特权和优势,可以经持有2/3以上该类别股份的股东书面批准,而以任何方式变更、修订、处置或影响……”
第59条:“公司可以通过特别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条件,从而开展以下活动:……(3)以法律授权的任何形式减少其资本……”
第62条:“公司原始资本的第1股至第6000股为4%累积优先股,其持有人有权优先从公司可分配利润中获取股息,股息按每年已付清或记为已付清优先股授权资本额4%的比例计算,这些股息应是累积的,于1月1日和7月1日每半年支付一次,且在公司终止时,优先股股东对这部分可分配利润享有优先主张权。”
第64条:“附于任何类别股份之上的特别权利、特权、优势不应在未经持有该类2/3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批准之前以任何方式变更、修订、处置或影响。”
第79条:“……在投票表决时,普通股股东就每一普通股享有一个表决权。除非公司在6个月内未按每年4%的比例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优先股股东无权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如果优先股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优先股股东就每5股优先股享有一个投票权。”
Cunliffe法官和Bryan Farrer法官支持反对减资的优先股股东,他们的主要论证是,减资方案导致优先股股东的股息减少,尽管因公司亏损而减资,但优先股应当享受固定的股息。如果每股面值减少到15英镑,优先股的股息应当增加到5.33%。当然,每股面值减少3英镑则无须主张增加股息,因为它被返还给股东。总的来说,价值12英镑的每股优先股在减资后应享受5.33%的股息。因此,公司章程第6条和第64条规定的优先股获取股息的权利在减资方案中发生了改变或修订,在1/3以上优先股的持有人反对减资方案的情况下,按照公司章程第6条和第64条,该方案不能实施。
Hon. Frank Russell法官、W. R. Sheldon法官和Astbury J.法官均认为,根据公司章程第59条和第79条的规定,公司通过普通股股东投票即可以任何法律认可的方式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公司章程第62条的规定,优先股的面值为20英镑,附于优先股之上的特别权利、特权或优势仅仅是对4%累积优先股股息享有的权利;第62条的规定不能妨碍公司根据第59条享有的权利,即在获得法院批准的前提下以任何法律认可的方式减资。并且,减资不构成公司章程第6条和第64条规定对任何特别权利的改变,因为优先股股息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根据章程第59条减资,这也完全符合章程第62条规定的优先股的权利。优先股只享有优先股授权资本额4%的股息(而授权资本是可根据章程第59条减少),而不是每股16英镑的股息。据此,驳斥了原告的第一个主张,即如果任何优先股被包含在减资方案中,在没有获得持有已发行优先股2/3的股东同意之前,公司无权进行减资。
Astbury法官进一步指出,如果优先股对资本不享有优先权,则因亏损而进行减资的损失应当由公司终止时所有承担损失的股东来承担,即如果公司既有普通股又有优先股,但优先股仅就股息享有优先权而对剩余资本分配不享有优先权,减资时的损失应由普通股和优先股平等分担。
此案判决的主旨是,在一个存在不同类别股份的公司,各类别股份按相同比例减少资本时,如优先股就资本不享有优先权而仅就股息享有优先权,则减资不构成对附于优先股之上的股息权的变更,尽管股息与公司的资本直接相关。
该判决后来在White v. Bristol Aeroplane Co. Ld.案中遭到NevilleGray Q. C.法官和Denis S. Chetwood法官的质疑,认为“其论证仅仅说明了权利是否被‘改变’( Altered)和‘修订’(Modified),但法官并没有讨论优先股的权利是否被‘影响’( Affected)‘影响’是一个含义最宽泛的词语”[2]。
(二)分拆股份不构成变更:Greenhalgh v. Arderne Cinemas Ltd案[3]
在Greenhalghv.Arderne Cinemas Ltd案中,被告Arderne Cinemas公司于1941年分别发行了面值10先令(50便士)和面值2先令(10便士)的普通股,两种面值的普通股在所有方面都享有相同的权利。公司章程规定,在投票表决时,每个成员就其持有的每一股普通股享有一个表决权。原告Greenhalgh持有被告大量的2先令股份,在“一股一个投票权”的安排下其可以控制40%的投票权,可以阻止股东大会通过特别决议。但是,在10先令普通股的股东的促使下,被告的股东大会通过了普通决议,将一股面值10先令的普通股分为5股面值2先令的普通股,且享有与原始普通股相同的权利。因此,原告提起诉讼,主张附于2先令股份之上的权利因该普通决议发生了变更。
Lord Greene MR.法官认为,当考察原始2先令普通股的地位时,遇到的问题是:于2先令普通股之上的有关投票的权利是什么呢?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附于该类股份之上的关于投票的唯一权利是与公司已发行的其他普通股一样,就其持有的每一股普通股享有一个投票权。而2先令普通股的这个权利并没有被普通决议剥夺,例如规定或试图规定其每持有5个普通股才享有一个投票权,那样才会构成对附于该类股份之上的权利的变更。但是,在此案中,并未发生类似事情,2先令普通股的“一股一个投票权”仍然存在,未受干扰。Lord Greene法官承认,普通决议的结果的确改变了原始2先令普通股的地位,原告原来的控制地位因此不复存在,在这个层面上,原始2先令普通股的权利的确“在商业意义上”受到了“影响”。但是从法律层面考察,Lord Greene法官并不认为,作为交易的结果,该类股份的权利被改变了,“他们仍然是他们自己,就其持有的每一普通股,与其他已发行(包括新发行)的普通股一样,平等的享有一个投票权”[4]。
从此案的判决论证来看,法官更加注重被“变更”权利本身在法律上的含义,而不在乎行使权利的结果是否在商业上受到“影响”。
(三)发行新股不构成变更:Whitev.Bristol Aeroplane案[5]
White v. Bristol Aeroplane Co. Ld.案是关于类别权利变更的另一个重要判例。其案情如下:
被告Bristol飞机公司拥有390万英镑的资本,其中面值一英镑的优先股60万股,以及面值10先令的普通股660万股。被告提出一项增资议案,建议将股本增加到588万英镑,增资方式为:增加66万股面值一英镑的优先股和264万股面值10先令的普通股,新增的优先股、普通股分别与原来的优先股、普通股享有同等权利。新增的优先股和普通股均向现有的普通股股东发行,以公司的储备基金支付股款。
实施该增资议案的结果是:(1)普通股股东获得66万股优先股,超过了既存全部优先股的一半,原优先股股东在优先股中的独占地位不但被打破,而且还沦为优先股的少数股东;(2)普通股股东的普通股股数增加,普通股与优先股的比例从原来的11:1变成了7.5:1,事实上提高了普通股的投票比例。
为此,公司发出通知召集所有普通股股东召开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此时,原告White,一个被告的优先股股东,代表自己和其他所有优先股股东提起诉讼,以该议案直接影响了优先股股东作为一个类别的权利和特权为由,请求法院:(1)禁止被告召集一个没有优先股股东参加的股东大会,以批准该议案;(2)如果优先股股东没有根据公司章程第68条的规定召开类别股东大会批准该议案,则禁止公司通过和执行该议案。
被告的公司章程中与本案有关的主要条款包括第62条、第68条和第83条。
第62条:“无论是否所有已授权的股份已全部发行或所有已发行的股份均已全部催收,公司都可以在任何时候经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增加资本,总增资额为一个特定数,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分为面值相同的若干股份。在保证附于特殊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增资所形成的股份可以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或(在股东大会没有规定时)董事会决议,享有特殊的权利或特权,特别是,可规定这些股份在获得股息时享有优先、劣后或获取资格的权利,或在参与剩余资产分配时享有特别的权利,或享有特殊的投票权或没有投票权。除非按照第68条获得优先股股东单独召开的股东大会的批准,增发的股份在获取股息或剩余资产分配上享有的权利不得优先于第61条规定的优先股。但是,只要已发行的·所有优先股资本额不超过已发行且公开出售的普通股资本额,新设或发行与优先股权利相同的股份则无须获得上述批准。”
第68条“权利的修改”规定:“影响、修改、改变、处置或废除附于构成公司资本的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或特权,均需获得该类别股份持有人单独召开的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本章程的所有关于股东大会的规定均适用于类别股东大会。”
第83条:“在受制于附于任何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或限制的前提下,在举手表决时,每一个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仅享有一个表决权,在投票表决时每个亲自或委托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就其每一股份享有一个表决权(对优先股而言,就每一英镑享有一个表决权;对普通股而言,就每10先令享有一个表决权)。优先股股东无权获得股东大会的通知,无权参加股东大会,也无权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下列情形除外:股息分配拖欠;股东大会的议题是解散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或其他直接影响到优先股作为一个类别股份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的议题。”
初审法官Danckwerts J。判原告胜诉,被告提起上诉。
上诉审中有两名法官Neville Gray Q. C.和Denis S. Chetwood同意初审法官的意见,他们认为,第68条在使用了修改、改变、处置、废除等词语后,仍加上“影响”一词,说明“影响”具有非常宽泛的含义。“影响”是所有上述用词中最宽泛一个。任何人都会合理的认为,优先股股东在投票权上的大多数地位将会为增资议案所“影响”。正如在Greenhalgh v.Arderne Cinemas Ld.案中所述,原告的权利尽管没有在法律上发生改变但在商业上受到了影响,应把关注重点放在优先股股东权利的价值而不是优先股的价值。在此意义上,优先股股东的权利受到了影响。
上诉法院的其他三名法官Evershed M. R.、Denning L.J.和Ro-mer LJ.则不同意初审法院的判决,认为增资议案没有影响优先股股东的类别权利,进而驳回了初审判决。以Evershed M. R.法官为代表,阐述理由如下:
根据被告的章程第61条,优先股股东享有三项权利:第一,较之普通股,每年优先获取已付清资本额5%的股息;第二,在公司解散时,较之普通股,优先获得尚未分配的股息和参与剩余资本分配的权利;第三,在第68条和第83条规定的情形下,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的权利。Evershed法官指出,显然,增资议案并未“修订”、“改变”、“处置”,更没有“废除”优先股股东的上述权利,因此,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增资议案是否“影响”了优先股股东的权利?
Evershed法官对初审Danckwerts法官将“影响”作最宽泛理解的观点并不赞同。他认为,如果反过来看待这个问题,将意识到,被影响的必须是优先股股东的权利。而增资议案是否影响到了优先股股东的权利呢?Evershed法官认为没有,因为,即便增资议案被实施,原优先股股东的权利仍然存在,章程第61条规定的三个权利均没有受到影响。尽管原优先股股东对其权利的享受和有效使用其权利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如前所述,原优先股股东无论在优先股还是所有股份中的比例均有下降),但是,“权利受到影响与权利的享受或将权利付诸实效的能力受到影响是不同的”。
Evershed法官还援引Re Mackenzie & Co.案和Greenhalghv. Ard-erne Cinemas Ltd.案,对用词及权利的理解进一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影响”和“改变”的确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但是本案的关键不在于“影响”和“改变”的区别,而在于“商业上的影响”和“法律上的影响”的区别。增资议案在商业上影响了优先股的权利,但是,根据公司章程以及对其相关条款的解释,在法律的意义上,增资议案并未影响优先股的权利。如果在任何商业意义上影响了优先股的权利,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优先股的价值或影响到对优先股权利的享受,就要召开类别股东大会,得到类别股东的批准,那对普通股来说,这个限制就太大了。
Romer法官补充到,由股东大会决议或公司章程授予的权利,除非经该类权利的享受者批准,不应被影响。但是,公司章程并不对行使权利的结果给予任何保证或担保,在任何方式下对行使权利的结果均不予保护。只有权利本身是受保护的。
此案以更加详实有力的分析再次肯定了Greenhalghv.Arderne Cine-mas Ltd.案的观点:对权利的影响和对权利享受(Enjoyment of Right)的影响是不同的,法律意义上的影响和商业意义上的影响是不同的。
五、借鉴
以《1985年公司法》第二章为代表的成文法规则和以上述案例为代表的判例法构成了英国类别股份制度的主体架构。成文法主要是规定了在附于特定股份之上的权利发生变更时,必须获得持有该类别股份的股东的适当同意,判例法则主要是在如何界定“类别股份”和“类别权利”,以及如何解释“权利的变更”这两个类别股份制度的核心问题上着墨,因为这两个核心问题在事实上决定了对类别股东的保护程度。
(一)以权利定股份、以股份定权利还是以股东定股份
就“类别股份”和“类别权利”的界定而言,将上述关于界定“类别股份”和“类别权利”的理论、成文法和判例法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1985年公司法》中,“类别股份”被定义为“具有相同权利的股份”,“类别权利”又被描述为“附于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这里将股份和权利相互对指,事实上是一个循环定义,对“类别股份”和“类别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均未进行界定。我们不禁怀疑《1985年公司法》的起草者是否也曾为界定这两个名词而大费脑筋,最终颇具心计地使用这样一个循环定义来回避这个问题。无论我们的怀疑是否确实,但其导致的结果则是无疑的:在定义类别股份时,关注的核心是附于股份之上的权利,权利相同则为同类股份,权利不同则为不同的股份类别;但在考察类别权利时,则不得不从“附于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出发,首先探究什么是“类别股份”又变成了逻辑的必然。这样,股份需要以附于其之上的权利来定类别,而权利又需以其所附之股份来定类别,相互纠缠,不得解答。
为此,英国的法官们和学者们开始了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争论和相互指责。
在Cumbian Newspapers案中,Scott j.法官认为,在《1985年公司法》中,“ Class Rights”的使用仅限于第二章的标题及其项下第125条和第129条的小标题,在正文中涉及类别权利,均使用“附于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 Right Attached to Class of Shares)字眼,可见“类别权利”只是“附于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的简约描述,二者的含义是一致的[6]。基于这一判断,Scott J.法官将划分类别的重点放在“权利”之上,“以权利定股份”,他指出,无论其是否持有被公司章程规定为相同类别的股份,如该案中原告持有普通股与其他普通股毫无差别,但只要原告持有的普通股享有特殊权利,这些特殊权利即为类别权利,进而原告所持的普通股也成为类别股份,原告构成类别股东。
但是,Scott J.法官的观点遭到了学者Eilis Ferran的指责。Ferran认为,Scott j.法官在决定《1985年公司法》第125条的适用时将“类别权利”和“附于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等同视之,这“值得进一步研究”[7]。他指出,即便在公司的股份资本被非常清晰地分为不同类别的情形下,解释类别权利的概念也存在三种可能的途径。第一种解释是,只要那些由该类别独享且不同于附于其他类别之上的权利才是类别权利。例如,附于双投票权普通股之上的唯一的类别权利是投票权,其股息权和资本权与只有一个投票权的普通股一样,就不是类别权利。这是最狭义的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所有由公司组织文件规定的附于某类别股份之上的权利都是类别权利,无论这些权利由某个类别独享还是同时也为其他类别享有。例如,附于双投票权普通股之上的股息权和资本权也属于类别权利。但是,这个解释的限制在于,公司组织大纲和章程的其他规定也可能构成类别权利,其结果是公司组织文件的任何变更都需要得到类别股东的同意。这是对“类别权利”最宽泛的解释。第三种解释是前两种解释的折中,即任何由类别股份独享的权利是类别权利,同时,关于股息、资本、投票以及类别权利保护的权利也都是类别权利,尽管在特定情况下不同的类别股份会在这些方面可能享有相同的权利。第二种从未得到任何权威或学者的支持,分歧主要在第一种和第三种解释上,这二者分别有判例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支持[8]。从Ferran对类别权利的解释看到,他将划分类别的重点放在“股份”之上,“以股份定权利”。
而Hellenic&General Trust案则从另一个角度对“类别股份”进行了诠释。我们注意到,在此案中,法官关注的重点从权利转向利益,关注的对象也从股份转向股东,因为,尽管所附权利相同的股份之间不存在不同利益的问题,但是即便拥有相同的股份和相同的权利,各股东的利益也可能不同。此案最后得到的结论是M公司构成“类别股东”(Class of Members; Class of Shareholders),这导致其持有的股份成为“类别股份”,这样的推理逻辑反过来则不能成立。此案判决显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1985年公司法》用词(Wording)的局限,但与股权、权利之争也不再是一个层面上的讨论了。
以权利定股份、以股份定权利还是以股东定股份?应该是从哪个角度为出发点,对类别权利、类别股份和类别股东进行界定?在英国类别股份制度上,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法官和学者们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的,只有一个潜在的准则,亦即Ferran的总结:“对类别权利的解释本质上取决于对少数利益的保护程度,对类别权利的解释越宽泛,对少数的保护就越多”[9]。
可见,类别股份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保护少数利益的机制,它是在“资本多数决”和“一股一权”的基础制度之上,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谈判的结果,利益博弈的过程,界定“类别权利”和“类别股份”的严格程度主要取决于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
(二)权利被“变更”还是变更的是“权利”
就“权利的变更”之解释而言,《1985年公司法》除了指明“变更”包括了“废除”之外,并未对“变更”进行定义,但一般而言,公司章程中相关规定会对“变更”做更加详细的阐释,如表达为“影响(Affected)、改变(Altered)、修订(Modified)、处置(Dealt With)、废除(Aborted)”等。从上述三个关于类别权利变更的判例来看,虽然也有法官尝试对“影响”、“改变”、“修订”、“处置”、“废除”等用词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影响”一词加以探究,尝试从这个角度为确认变更的发生寻找出路,但是,这条出路由于在逻辑上欠缺周延性而不具有足以影响判决的说服力,因为,尽管法官们在对这些用词的理解上并没有实质的差异,三个判例的最终判决均没有在“变更”的阐释和解释上多费口舌,但是法官们更关心的是“被变更的是什么”,而非“变更本身是什么”。
对于“被变更的是什么”的回答,三个判决在观点上体现了惊人的一致:在Mackenzie & Co.案中,Astbury法官一再强调,优先股股东仅对股息享有优先权,对资本没有优先权,股息优先权的比例为4%而非其他;在Greenhalgh v. Arderne Cinemas Ltd.案中,LordGreene MR.法官则直接指出,被变更的应该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而非商业意义上的行使权利的结果;在Whitev.Bristol Aeroplane案中,Evershed法官更是淋漓尽致地论证了权利和权利的享受是不同的,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的变更才受到保护,商业意义上权利的享受被变更不会受到保护。其他相关判例亦是如此,如在1901年的Underwood。London Music Hall, Limited案[10]中,Kirby法官认为,优先股股东的权利是优先享受7%股息,公司发行新的优先股和普通股没有变更这些权利;在1913年的Re Schweppes, Limited案[11]中,Coz-ens-Hardy M. R.法官以同样的理由指出,公司发行新的普通股没有变更优先股的任何优先权利;在1953年的Re Old Silkstone CollieriesLD.案[12]中,Evershed法官用冗长的篇幅论证了公司通过特别决议赋予了优先股新的特殊权利之后,才得出结论,注销优先股构成对这些权利的废除。这些关于类别权利变更的判例,再次将关注的重点转回到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对类别权利的界定和解释上。
有趣的是,关于界定类别权利的判例与关于确定变更的判例,在解释“类别权利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似乎相互矛盾,前者倾向于将类别权利做宽泛的解释,甚至从权利的不同突破到利益的不同,而后者则狭窄的将类别权利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完全否定商业意义上的权利行使结果。这又是何道理呢?需要回到类别股份制度的本质上来找原因。在前述Ferran的总结中已经涉及,类别股份制度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少数股东、少数股份的权利和利益。《1985年公司法》第125条类别股东表决机制的起源是,防止公司根据第9条以特别决议修改章程而变更或废除作为少数的类别股份,如无投票权的优先股的权利时,持有该类股份的股东对之毫无发言权或其投票权被其他类别的股份所淹没[13]。正如Palmer's CompanyLaw中说道,当一个公司的资本被分为等额股份时,股份之间被默认为享有相同的权利,每一股份的控制力是一样的,股东持有越多的股份就对公司享有越强的控制力,这是伴随公司而生的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原则。在类别权利变更时,之所以需要类别股东的单独表决或同意,除了其在一般情况下根本就不享有投票权的情况外,主要都是因为通常类别股东是少数,其投票会被多数的投票所淹没而失去控制力,为了给予这些少数股东特别的保护,英国公司法特别赋予其单独表决或同意的权利。但是,这些特别权利显然只是股份平等、股份民主原则的例外,是在默认“资本多数决”的前提下对少数的特别保护。而给予少数特别的保护,本质上是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谈判的结果,利益博弈的过程:在一个公司中,不仅需要多数股东的参与,也需要少数股东的介入,多数和少数之间相互需要,但双方的利益却不完全一致,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下,多数股东处于优势地位,其可能利用优势地位通过剥夺少数股东,而非通过促进公司的成长来牟取一己之利[14],少数股东对此则颇有戒心。为了使得相互需要的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能够达成合作,给予少数股东特别保护以防止多数股东滥用其优势地位损害少数利益,则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也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类别股份制度则是保护少数利益的机制之一,是多数和少数利益平衡的结果。
由上可知,类别股份制度在规则和解释上的倾向性取决于对少数利益的保护程度,而对少数的保护程度取决于在特定的地区、时代、经济、市场和个案背景下,多数与少数相互之间的供需关系和谈判中的强弱均势,最终取决于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利益平衡。这种微妙的利益平衡显然已为英国的法官们意识到了,并且在判决中不懈的尝试寻求最佳的利益平衡点:在Greenhalghv.Arderne CinemasLtd.案和Re Old Silkstone Collieries LD.案中,引起争议的特殊权利直接被公司提出的议案废除了,这显然是对这些权利的很严重的“冒犯”,此时,法官尝试将这些权利做扩大解释,将天平偏向少数一方;在Hellenic & General Trust案中,如果收购决议被通过,少数股份将不复存在,也是一个严重的“冒犯”,法官的天平同样偏向少数;相反,在Mackenzie&Co.案、Greenhalghv。Arderne CinemasLtd.案、White。.Bristol Aeroplane案等一系列纠缠于“改变”、“修订”、“影响”的案件中,法官就显得比较慎重了,“变更”显然是比“废除”小许多的“冒犯”,何况“变更”程度之本身就存在较大的可伸缩度呢?更重要的是,这些被怀疑变更了类别权利的议案,同时都是普通股根据其几乎是天经地义享有的减资、增资、调整股本结构等权利而进行的,类别权利是否足以对抗管理公司的普遍权利呢?类别股东商业上的利益是否足以对抗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为整个公司带来的利益呢?保护少数类别股东的意愿是否足以对抗保护多数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意愿呢?法官的回答是否定的。
由此可见,在界定类别权利及其变更时,无论是扩大的解释,还是狭义的理解,法官们的共同初衷都是寻找多数和少数之间那个微妙的利益平衡点,只是因为每个案件的案情和经济背景不同,法官们需要根据个案的特定背景斟酌如何既适度又公正地保护类别权利。也就是说,这个利益平衡的权衡标准,因特定的地区、时代、经济、市场和个案背景不同而各有差异。 [1][1916] 2 Ch. 450.
[2]White v. Bristol Aeroplane Co. Id. [ 1953 ] Ch. 65.
[3][1945] 2 All ER 719, [1946] 1 All ER 512, CA.
[4]张明澍编:《英国公司法经典案例》,222-22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1953] Ch. 65.
[6]Cumbian Newspapers Group Ltd. v. Cumberland&Westmorland Newspaper and PrintingCo. Ltd.[ 1987] Ch. 1.
[7]Eilis Ferran, Company Law and Corporate Fi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 33.
[8]Eilis Ferran, Company Law and Corporate Fi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338.
[9]同上注,339页。
[10][1901] 2 Ch. 309.
[11][1914] 1 Ch. 322
[12][1954] Ch. 169.
[13]Paul L. Davies, Gower's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Sixth Edition),London,Sweet&Maxwell, 1997, pp. 717-718.
[14]Bernard Black, Reinier Kraakman, Anna Tarassova著,彭冰译、董炯校:《俄罗斯私有化与公司治理:错在何处?》,载《清华法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又见Lucian Arye Bebchuk,Reinier Kraakman and George G. Triantis, Stock Pyramids, Cross-Own-ership, and Dual Class Equity: The Creation and Agency Costs of Separating Control From CashFlow Rights, concentrated corporate ownership, R. Morck, Ed, (445-460) 2000; Simon John-son,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 de 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unnel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Proceedings, May 2000.

2006 > 2006年总第7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