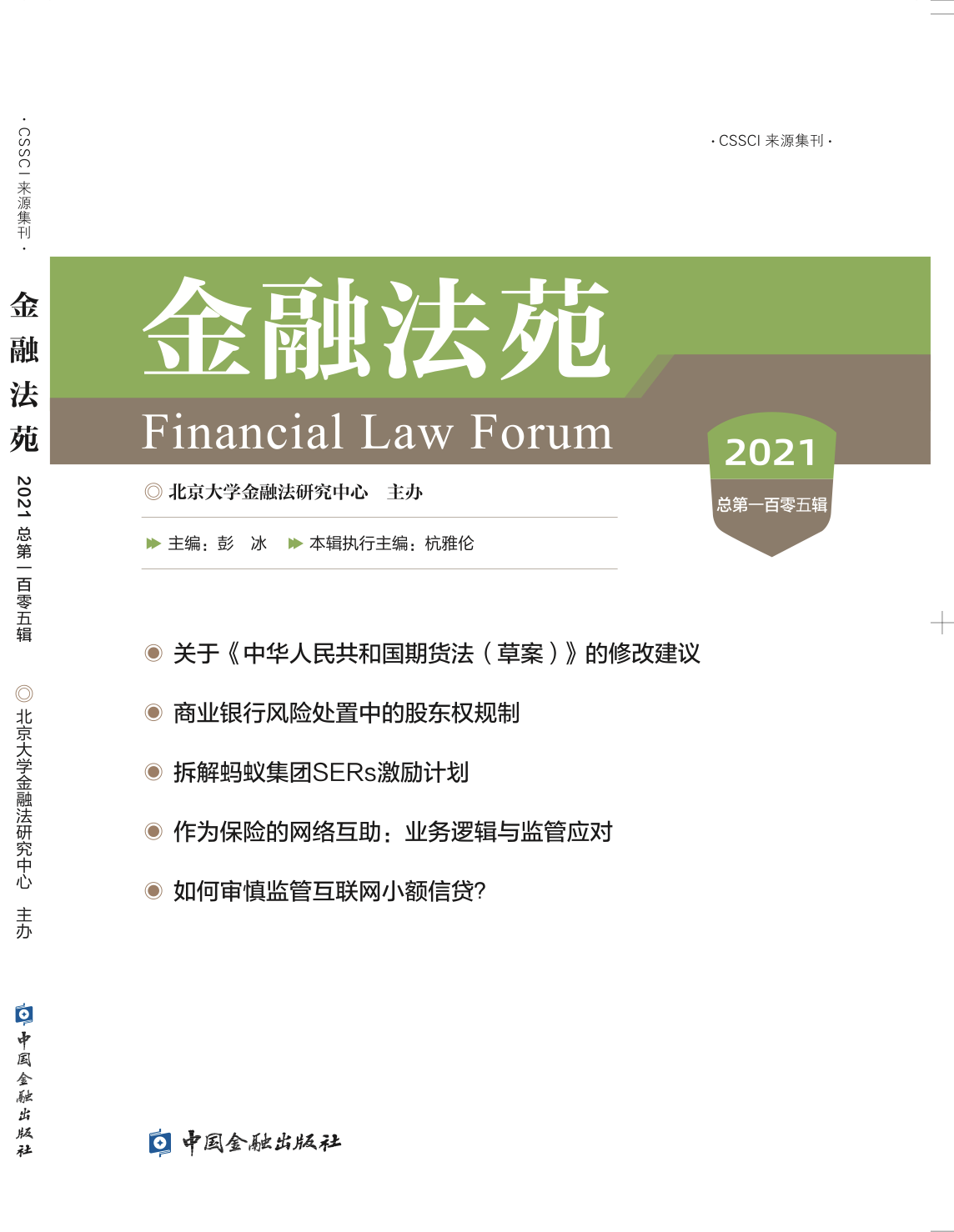始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代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如今欧债危机余音未散,全球经济增长依然趋缓,危机尚未真正结束。不禁要问,监管机制如何构建,才能保证我国等后发国家在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将系统性金融风险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1}其中,如何约束金融系统的风险节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成为不能回避的重要议题。
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宏观审慎视野下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
从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引发次贷危机,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致使全球性金融恐慌。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全球建立的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在拥有巨大破坏力的金融海啸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中,金融机构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不断增强,进而导致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不断强化,而现代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发展也使得风险的相关性和复杂程度不断增加。那么致力于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定的微观审慎监管自然不能降低单个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带给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在反思危机过程中,强调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内容的宏观审慎监管(Macropmdential)在短时间内引起世界关注并迅速付诸实践。{2}与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关注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更加重视金融系统的内生性风险而不仅仅只重视外生性风险。{3}虽然学界尚未对宏观审慎监管范畴形成统一认识,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和监管是公认的重要维度。{4}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是和系统性风险相伴相生的。金融危机表明,系统性风险是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或可能{5},而某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又是足以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内生诱因。因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相关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金融机构。
(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传导机制
一般认为,系统性风险可分为两类:一是系统性金融风险(Systemic Finanical Risk),是指一个冲击将导致经济价值与信心的损失,以及整个金融体系不确定性的风险;二是系统性实体风险(Systemic Real Risk),是指一个冲击将导致实体经济部门严重受损的风险。{6}所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困境可在以下两个方面迅速蔓延乃至拖垮经济体系。
一方面,某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服流中断时,借助金融系统内部基于流动性需求形成的资产负债关联和市场参与者的悲观心理预期,催生一系列金融机构的连锁倒闭,进而可能造成整个金融系统或者部分金融系统的崩溃。{7}另一方面,当金融服务中断被认为具有系统性时,对实体经济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通过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供求的影响体现出来,且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逐渐体现。{8}也就是说:最初只是某个机构或市场内的冲击,最终可能导致各个金融部门和实体乃至全球范围经济动荡与萧条的风险,比如雷曼兄弟破产不只引发了华尔街的“腥风血雨”,也在极短时间内导致通用集团的“弹尽粮绝”。{9}
正因为如此,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围绕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和指导性文件。比如,2010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巴塞尔协议Ⅲ》,2011年7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解决方案——建议和时间表》,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全球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和额外损失吸收能力要求》等。
(三)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虽然中国金融业整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直接损失很少;但这不能说明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存在系统风险性。美国波士顿联储主席埃里克·罗森格伦(Eric S. Posengren)曾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分为两类:一是大型高度杠杆化机构,其资本损失对经济产生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其倒闭会对国内和国际交易对手产生极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0}
很明显,诸如雷曼等大型投资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源于其高负债经营带来的高杠杆率和关联交易以及影子银行体系所带来的风险传染。而我国大型金融机构似乎以上问题并不严重: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开放程度,诸如五大商业银行的规模在世界范围内虽已名列前茅,但从互联性角度,特别是国际影响角度,中国现有金融机构的国际互联性和影响性都相对较低,其中一家财务状况的恶化难以对国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显著传染和负面影响。{11}而且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商业银行在存贷比等方面又面临全球最为严格的限制,因此我国的金融机构杠杆率并不高。
但恰恰是由于现有金融体制导致我国存在若干体制性风险。比如,融资渠道过分单一,高度依赖信贷资金,金融风险高度集中。据统计,2011年年底,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已达54.79万亿元,银行业存量贷款十分巨大,资本压力持续增加。以房地产市场为例,据人民银行对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的分析,有55%的资金直接来自银行系统,如果加上施工企业垫资中的银行贷款,住房开发项目实际对信贷资金的利用占其资金总规模70%以上,房地产市场存在对信贷资金的单向依存关系。{12}
融资渠道单一在某种程度上会催生系统性风险。实体经济对信贷资金的过分依赖会将市场风险和融资信贷风险集中到银行,转变为银行的信贷风险。{13}此时,突发的急速滑落会造成银行系统的资金链断裂,发生银行失败。在一家或几家银行失败后,因银行间广泛的债务、债权链条关系、存款者的信心动摇导致银行挤兑、外部投机性攻击、过于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和关系贷款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单一的银行失败事件扩散成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或经济危机。因此着力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二、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离不开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和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比较和分析。
(一)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与确定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与确定是监管的逻辑前提。适当评估标准的缺失很可能导致识别不足或者过度识别。一方面,识别不足会导致监管真空,直接削弱监管效果;另一方面,过度识别意味着增加监管成本并降低金融效率,直接损害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并且,过度管制可能催生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导致“猫鼠游戏”陷入恶性循环。但应承认,任何评估体系都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利用现有的系统性风险模型预知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系统性风险因素是时刻变化的,金融网络中任何初始因素的变化都会产生“蝴蝶效应”而改变结果。因此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必须充分考虑各因素的动态变化,不断识别新的风险来源。
就目前来看,学界尚未对评估标准形成统一认识{14},但规模、关联性和可替代性无疑是公认的重要参考因素。这种观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的《关于评估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系统重要性指引》中得到体现。笔者认为,上述标准综合考虑了直接和间接两个影响渠道,应在我国予以参考。规模和可替代性是从直接影响角度衡量的,而间接影响的大小依关联性的强度而定。
一般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与其能给系统提供的金融服务数量成正比。从数据上看,机构资产负债表内和表外风险暴露规模、参与交易规模、库存或者管理资产规模,从不同角度表明其客户资金匮乏的程度、其与其他机构的业务可能中断的程度、其交易对手可能面临的损失程度。机构特定的业务模式和组织结构对规模标准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此外,虽然某类机构规模不大,但可能因它们在经营模式、关联资产或者负债的风险暴露、风险管理方法等方面十分类似,易于在同时陷入困境,或者在面对危机时有十分类似的行为反应,这一类机构的总体规模也被视为十分显著。
关联性是指由于机构经营中的契约性联系网络,某机构陷入财务困境引发其他机构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这种连锁反应对资产负债表的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同时产生作用。金融机构贷款方和客户的数量越大,引发对客户或借贷者的溢出效应的潜在性越高。此外,单家机构的风险暴露规模越大,潜在效应越被放大。一个体系网络内关联的复杂性,以及当一个系统的核心因素遭受压力时的信心因素,都能增加市场参与者的不确定预期,进而扩大系统性风险。
可替代性是指当单个机构处于危机状态时,其所处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难以提供相同或者相近的金融服务以保证金融服务不至于中断,进而加剧系统性风险,例如,承担提供清算、交易的支付和结算或者保管服务等重要基础设施服务的机构。
(二)国际社会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措施
雷曼破产对全球金融秩序的破坏性打击成为国际社会确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目标的重要参照,监管机构力争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破产效率和缓解破产时的共振效应。{15}进而,国际社会在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处置三个层次着力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安全网”。
1.事前预防: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抵御风险能力。高负债经营带来的资金缺口导致的抵御风险能力减弱是金融危机肆虐华尔街的重要原因。国际社会认为应采取有效措施,在危机发生前,引导系辨重要性金融机构降低规模及彼此在业务风险上的关联度,提高资本要求,提高损失吸收能力,防止过大和过于复杂金融机构的出现,从根本上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订资本协议,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
《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设置资本附加;附加资本充足率为1%,最大限度降低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16}除资本附加外,新资本协议还通过流动性附加、大额风险暴露限额和限制风险暴露集中度等其他政策工具来控制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降低其复杂性和关联度,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比如,在一般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应高于100%的基础上,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施加乘数要求。又如,限制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单一(或关联)客户的风险暴露集中度,该集中度不得超过监管要求比例,并在达到更低比例时要向监管机构报告。{17}
第二,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应急机制和自救安排。
应急和自救安排是指通过合同或法律的形式,可将用核心一级资本表示的附加资本按一定的比率转换为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务工具,以确保债权人能够承担系统重要性银行之损失的危机处置做法。具体表现形式是在银行风险加大或处于紧急状态时,要求银行将次级债或可转债按一定比率转换成普通股。{18}
第三,征收金融结构税、促使外部风险内部化。
个别机构不可能内化其对金融系统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必须通过征税或者其他严格的量化措施,对个体机构的风险行为加以限制,以产生事前激励降低系统性风险。{19}但系统性征税如果作为事前措施,则与实施附加资本的本质相似,均是通过提高资本以增强资产负债弹性,故更多学者支持以征税收入作为风险处置资金或政府处置预算的一部分,从而由股东和债权人而不是纳税人来承担危机成本和相应损失。{20}但笔者认为金融结构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对约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冒险经营作用不大。
第四,推行“简约金融”、施加结构限制。
结构性措施目前包括限制银行经营范围,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限制银行的规模,分拆过大银行;对外资银行子行和分行实施独立的流动性要求等结构性监管措施。虽然国际层面尚未对结构性措施达成一致,但部分国家已有实践,比如美国饱受争议的“沃尔克规则”。其核心要求是:除特殊情况,商业银行一般不得从事自营交易。商业银行对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银行一级资本的3%以及基金资本的3%,并且禁止银行做空或做多其销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
2.事中监管: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有学者认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出现后,应提高其稳健经营概率,尽可能地降低其倒闭可能性,表现为强化监管、提高监管标准。结合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强度与有效性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发达国家监管当局根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金融体系的风险影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求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建议》要求监管当局应有适当授权、独立性和资源,可独立采取监管行动,并获得足够的监管资源(数量和质量),以确保监管行为有效。部分成员国据此进行多项改革。比如,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分析识别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经营困境或经营失败对金融稳定造成的风险。同时,赋予美联储更多的权力,美联储有权要求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接受美联储监管,有权拆分对金融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机构。又如,英国进一步强化英格兰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加强英格兰银行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者的职责。{21}再如,欧盟设立首个超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微观层次上,设立分别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实施监管的监管局;宏观层次上,成立主要由成员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在必要情况下建议应采取的措施。{22}
此外,各成员国着力构建适当机制尽早识别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纠正和防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安全和不稳健的经营行为。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其非现场监测和预警,及时识别并处置风险;与此同时,提高现场检查频率,确保监管政策的贯彻落实,化解银行潜在风险。以欧盟为例,新监管当局有权对特定的金融交易实体、金融产品和裸卖空等金融交易行为展开调查,以评估它们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监管局将有权临时禁止或限制某项金融交易活动或金融产品,并可提请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永久性禁止这类产品和活动。
3.事后处置:建立有效处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框架。如果新监管框架未能有效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危机发生后应通过制订周密可行的危机处置方案,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即使在危机期间也不至于对宏观金额稳定造成过大损害,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第一,审慎选择危机处置方式。
要在注资援助和正常破产之间进行谨慎决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旦陷入困境,政府往往被置于两难境地:任其倒闭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但救助又会导致道德风险、引发“大而不倒”难题。不合理的政府救助会产生诸多“副作用”。一方面,政府公共财政救助等特殊保护政策使得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可以逃避本该承担的风险责任,由此会促使其日后从事经营业务时冒更多、更大的风险。{23}另一方面,政府隐性担保将给普通大众带来强烈的信号,从而弱化利益相关者对金融机构的制约和监督。
第二,建立全面的风险处置制度和处置工具。
金融稳定理事会认为风险处置机制包括两方面措施:一是稳定措施。包括向第三方(直接或通过过桥机构间接)出售或转移风险机构全部或部分股权、业务,或由官方指定机构提供重要功能、由债权人提供资金、实现债务重组,确保系统重要性金融服务、支付、清算和结算功能不会中断。二是清算措施。包括有序关停部分或所有机构业务,按照存款保险机制和投资保障机制,保护储户、保单持有者和其他零售业务客户的资金安全。
第三,健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跨境危机处置机制。
金融一体化导致的金融互联要求国际社会完善法律制度安排,赋予处置机构开展跨境合作和信息交换的法律权利,废除法律中可能阻碍公平跨境处置的条款。金融稳定理事会力争明确母国和东道国当局在机构处置中的作用、责任和义务;母国与东道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建设危机时期的信息共享机制,消除信息缺口;建立有效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通过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协调各方,形成全球意义上的监管合力,从而严格、准确地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
三、中国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应关注的若干问题
此次监管改革对中国金融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在于发达国家金融系统为应付危机出现业务收缩,让出部分发展空间;挑战则要求还未成熟的中国金融业直面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同样的竞争和监管环境。因此,我们应结合自身国情,正确评估中国金融监管的发展现状,制定符合国情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
(一)中国现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综述
在反思危机和重建金融监管体系的浪潮中,我国已开始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
首先,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要求:“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制定跨行业、跨市场金融监管规则,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其次,2011年银监会制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要求根据国内大型银行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实践,从市场准入、审慎监管标准、持续监管和监管合作等方面,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24}最后,2012年银监会公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以下简称《资本办法》),此规定被称为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办法》全面引入《巴塞尔协议Ⅲ》确立的资本质量标准及资本监管最新要求,涵盖了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等多层次监管要求,促进银行资本充分覆盖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和个体风险。{25}
(二)中国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应关注的若干问题
因知识水平有限,笔者无力提出我国未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完整框架,仅结合前述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特殊国情,提出应重点关注的几个方面。
1.正确平衡强化监管中政府干预和市场选择的关系。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平衡政府干预和市场选择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欧美大型金融机构,新监管要求大幅度地提高了政府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干预能力,它们将更多面临来自监管部门的外部压力和影响。
出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金融业,虽然市场化改革已取得重大成功,但我国对金融机构的政府干预一向较多。因此在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过程中,应注意在从严监管与适度监管中寻求平衡,在平衡过程中要抓住核心问题,不应过多干涉银行的日常经营。毕竟当前的中国金融业正处在由传统赢利模式向现代赢利模式的转变阶段,特别是作为中国“走出去”代表的大型商业银行,还需要给予一定的自由度让其在市场大潮中“摸爬滚打”,并给予其经营的较高独立性,不应束缚太紧。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约束应着眼长远,不应因短期市场变动带来的或有压力而要求其频繁改变经营战略;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也需要抓住核心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而对于具体的经营模式、业务方向,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等具体化的问题应当全权交由商业银行自身来处理。这是在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时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2.监管框架构建应基于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正确评估。与欧美相比,中国金融业仍以传统业务为主,微观个体经营模式上的同质化风险和带来的经济动荡更应关注。
在我国,除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外,影响宏观审慎的其他体制性因素也足以引发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系统性风险有可能来自于以下方面:(1)宏观经济周期性的调整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2)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变化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抵押资产价格下跌或财政收入下降,就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4)汇率波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很强,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5)由通货膨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强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应把非正规金融、地方金融、房地产金融市场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等纳入系统性风险监管和控制的范围。
此外,我国银行业发展受到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再加上不同银行从发展战略到客户定位等严重趋同,加剧了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性。因此,金融创新不足、同质化经营也是我国系统性风险的诱因。因此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鼓励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发展,发展多元化、异质化的金融业务模式和业务品种,构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例如,在最近提出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要求问题上,各大型银行很有可能通过市场融资来满足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甚至可能出现新一轮融资热潮。但继续融资并不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对监管新政的有效策略,从银行自身角度来看,应当在所承担的风险和业务扩张的速度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改变过去单一依靠存贷差和贷款规模的扩大提高利润的局面,转变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来增加市场竞争力。
3.制定符合国情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虽然中国银监会2011年《指导意见》已要求未来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主要考虑规模、关联性、复杂性和可替代性等四个方面因素,但尚未制定具体标准和监管措施。笔者认为,未来我国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采用定量指标和定性判断相结合的方法。
借鉴国际经验,定量指标应包括《指导意见》所指规模、可替代性、关联性和复杂性四个指标;而定性判断则要考虑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内控机制、风险管理能力、风险传递机制等因素,由负责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部门会同行业监管机构共同作出判断。同时,要实现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全覆盖。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应不限于资产规模大的银行,还应包括大型保险公司,组织结构复杂、业务多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提供支付结算等基础设施服务的机构,以及资金规模大、投资行业多的私募股权基金等。{26}
另外,中国金融业中的政策扶持对象,特别是区域性农村金融机构,对区域性农村金融活动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故中国金融业的严峻挑战也有可能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大而不倒”机构,而是来自于这样一些目前监管不太充分的小型机构。{27}
4.整合监管体制,实现监管机构的协调。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诸如招商、平安、中信等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不断出现,法律框架下的分业经营遭遇到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是以防范行业风险和单一机构风险为目标的,难以应对日益系统重要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虽然存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间的协调机制,但现行监管框架内,信息资源分散、协调成本较高等问题制约了监管效能的提升。由于宏观审慎监管旨在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和联动就成为降低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措施。
强化中央银行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中的作用,是世界金融监管改革的趋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取向和对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分享程度,关乎金融业的宏观审慎管理。因为只有中央银行才是对金融市场流动性有最终调控能力的一方,要防止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就应该充分地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28}笔者建议借鉴美英等国的做法,赋予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由人民银行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日常事务,全面监测、评估宏观经济变化对金融系统稳健性的影响,评估整个金融系统的资本、流动性以及杠杆率可能产生的风险,监管跨市场和跨机构的金融风险等。而微观审慎监管方面则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作出规定。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实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无缝对接”。
四、结论
某种程度上说,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运营情况是整体经济金融健康度的一种综合反映,既受金融业自身监管水平的影响,更受其他各经济部门的运行状况,以及一系列特定的决策约束条件的影响。换言之,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似乎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它会受到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多维制约,特别是在面临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的中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势必具有某些语境化的独特需求。本文只能算是抛砖引玉。毕竟,一个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来寻找答案。 {1}刘春航:《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原因及其评估》,载谢平、管涛、黄益平、魏加宁、阎庆民、袁力、钟伟主编:《金融的变革》,2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得到广泛关注,但宏观审慎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库克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的前身,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就已被提出。当时的表述为:“委员会所关注的微观经济问题中的微观审慎问题,一旦开始融入宏观经济问题时,就应该被称为宏观审慎问题。委员会对宏观审慎问题保持合理关注,并把这些问题与委员会关注范围内的宏观经济问题联系起来。”
{3}CEV Borio. Towards a Macro - prudential Framework for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Lecture prepared for the CESifo Summer Institute 2002 Workshop on “Banking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Venice, July 17-18,2002.
{4}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实施前瞻性拨备制度、强化流动性监管、引入杠杆率监管、强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加强场外衍生品监管、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加强薪酬监管、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等。张显球:《宏观审慎监管:理论含义及政策选择》,序言第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5}Kaufman,G. and E. S. Kenneth,What Is Systemic Risk, and Do Bank Regulaors Retard or Contribute to It?, The Independent Review, Vol.,No.3,2003.
{6}De Niolo, G. and M. Lucchetta, Systemic Risk and the Macroeconomy, IMF Wp/10/29,February,2010.
{7}丁灿:《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形成与监管》,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8)。
{8}陈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的构建》,载《西部金融》,2012(1)。
{9}[美]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著:《大而不倒》,巴曙松、陈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张显球:《宏观审慎监管:理论含义及政策选择》,129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11}钟伟、谢婷著:《迷路知返》,20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12}洪艳蓉:《房地产金融》,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3}张雯著:《中国房地产信贷风险度量与控制》,47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14}目前评估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标法。在理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核心特征的基础上,直接给出界定指标,根据不同的金融体系发展状况界定不同的指标值,由此确定该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另一类是市场法。利用金融机构相关指标市场波动数据,通过衡量单个金融机构对整个体系的风险贡献程度,测定其系统重要性。由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监管机构最终采用指标法作为评估标准,限于篇幅,故市场法不予介绍。请参见徐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识别方法综述》,载《国际金融研究》,2011(11)。
{15}甄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确定及其面临的挑战》,载《银行家》,资料来源:http://money.163. com/12/0710/14/862E9MEQ0025335L. html,2012年7月12日最新访问。
{16} BCBS, The Basel Ⅲ Acord, From the Basel Ⅲ Complianc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BiCPA)[ EB/OL], http://www. basel - iii - accord. com,2000.
{17}陈军:《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标准的构建》,载《西部金融》,2012⑴。
{18}肖振宇:《系统重要性银行定义及其风险防范》,载《金融论坛》,2011(11)。
{19}Acharya, Viral, Lasse Pedersen, Thomas Philippon, and Matthew Richardson, Regulating Systemic Risk,in Viral Acharya and Matthew Richardson ( eds.),Retoring Financial Stablity: How to Repair a Failed System, Wiley, March, 2009.
{20}王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囯际监管改革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载《金融发展评论》,2011(8)。
{21}王刚:《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发展沿革、解决方案与政策启示》,载《上海金融》,2012(2)。
{22}潘林伟、吴娅玲:《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载《南方金融》,2011(5)。
{23}李玥:《“大而不倒”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中国市场》,2012(13)。
{24}该《指导意见》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主要有五方面内容:(1)明确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定义。(2)维持防火墙安排,改进事前准入监管。(3)提高审慎监管要求。(4)强化持续监管。(5)加强监管合作。
{25}《资本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除本办法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外,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应当计提附加资本。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1%,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认定标准另行规定。若国内银行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所适用的附加资本要求不得低于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规定。”
{26}王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国际监管改革进展及对我国的示》,载《金融发展评论》,2011(8)。
{27}钟伟、谢婷著:《迷路知返》,20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8}吴晓灵:《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看“大而不倒”问题的处置》,载《中国金融》,2010(16)。

2012 > 2012年总第8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