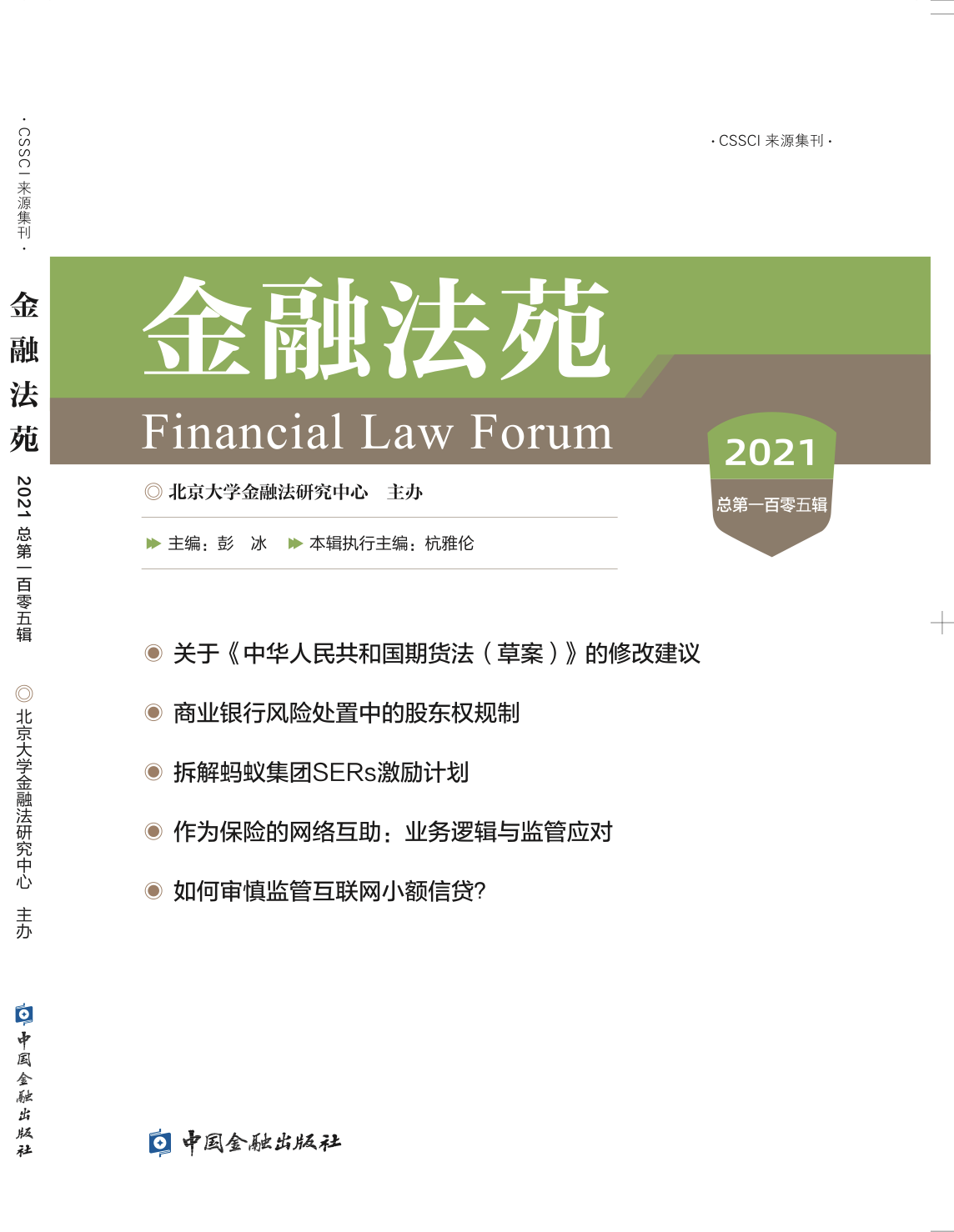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作者】钟维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营商环境跨学科交叉平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和征求意见。我们在此就《草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修改方向提出如下建议。
一、第三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草案》第三条的规定存在四个问题,分述如下。
1.与《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相比,《草案》第三条第一款所采用的是广义的期货概念,立法意图是用“期货”概念来涵盖包括狭义的“期货”和“期权”在内的所有场内标准化合约。但在此种立法格局下,只要在本法其他地方再出现专门针对期权的规定,在解释逻辑上就会出现问题。
例如,第三条第二款是针对场外衍生品的规定,其中包括”非标准化的期权合约”。就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即标准化的期权合约根据第一款叫“期货”,而非标准化的期权合约根据第二款叫“期权”。
再如,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讲的是期货合约的交割方式,第二款讲的是期权合约的交割方式。前面第三条把两种合约都涵盖在“期货”概念下,在这里却又分开表述两种合约的交割方式,显然采用的是狭义的期货和期权概念。
然而,第四十八条规定:“期货交易的交割或者行权,由期货结算机构组织进行。期货交易的交割包括实物交割、现金交割。”该条中“期货交易的交割或者行权”的表述换成了广义的期货概念,因为“行权”是只有期权合约才有的。
因此,建议保留《条例》中对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分别定义的方式,并规定“除另有规定外,有关期货的法律规定准用于期权”,同时对整部法律相关条文的表述重新进行梳理。
2.第三条第一款将期货定义为“由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将来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同时第三款对其中的“标的物”作出了界定,“包括农产品、工业品、能源等商品、服务及相关指数,以及有价证券、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及相关指数等”。在法律解释上,意味着期货合约交割时只能交付这些对象。然而,指数、利率、汇率合约等都是无法实物交割的,采用的是现金结算的方式,现有的立法表述方式无法涵盖现金结算方式。
因此,建议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法所称期货,是指由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将来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进行交割的标准化合约。”这样就能与第四十八条的“期货交易的交割包括实物交割、现金交割”衔接上。
3.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场外衍生品,但是采用了“其他衍生品”的表述:“本法所称其他衍生品,是指价值依赖于标的物价值变动的、非标准化的远期交割合约,包括非标准化的期权合约、互换合约和远期合约。”目前场外衍生品有一种标准化的趋势,而且场外衍生品标准化也是被鼓励的。但是,该款的立法表述方式无法涵盖场外的标准化衍生品。同时,“远期交割合约”的表述方式也容易与狭义的远期合约混淆。
因此,建议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法所称其他衍生品,是指在期货交易场所之外交易的,价值依赖于标的物价值变动的、非标准化的远期未来交割合约,包括非标准化的期权合约、互换合约和远期合约。”
4.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期货交易和其他衍生品交易的标的物包括农产品、工业品、能源等商品、服务及相关指数,以及有价证券、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及相关指数等。”期货及衍生品交易是一种双层标的法律结构,[1]其中,期货交易及衍生品交易的标的是期货及衍生品合约,期货合约及衍生品合约的标的是各种基础资产。因此,该款的表述是不准确的。此外,该款对合约基础资产的列举无法涵盖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标的资产。
因此,建议将第三条第三款修改为:“期货交易合约和其他衍生品交易合约的标的物包括农产品、工业品、能源等商品、服务及相关指数,以及有价证券、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及相关指数等,以及其他依合约安排能够决定合约价值的基础资产。”
二、第七条
《草案》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利率、汇率期货由国务院依法另行规定。”
该款第一句来自《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对期货市场的集中统一监管,《草案》与之相比其实是倒退了,人为割裂了对期货市场的监管。这样会产生若干问题,例如,跨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管辖权问题;再如,证监会多年来已经建立了包括交易、结算、保证金监控、风险监控等一整套期货市场及监管的基础设施,如果将来国务院规定利率期货和汇率期货专属于央行管辖,那么这两种期货的交易和监管是用证监会已经建立的监管体系,还是央行另建一套?可以理解,利率、汇率对于我国金融安全有重大意义,因此相关期货合约的上市及规则制定应当符合央行的政策。但是期货市场的行为监管并非央行所擅长的,而且不同机构监管间的漏洞有可能被违法者所利用,因此应当专属于证监会。
因此,建议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利率期货和汇率期货由国务院依法另行规定的上市及相关规则制定应当征求中国人民银行的意见。”
三、第二十一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
《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依照期货交易场所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
发生本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导致期货交易价格出现重大异常的,期货交易场所按照业务规则可以取消交易或者调整交易价格,并及时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公告。
对依照前款规定采取措施造成的损失,期货交易场所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存在重大过错的除外。”
然而,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异常情况”仅仅包括:(1)在交易中发生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2)发生不可抗拒的突发事件;(3)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3)种情况要求证监会事先规定,因此实际上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只有前两种情形。
但是,这两种情形明显无法涵盖期货交易场所按照业务规则需要取消交易或者调整交易价格的情形。与之相比,第九十五条列举的情形更加全面:“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重大技术故障、重大人为差错等突发性事件而影响期货交易正常进行时,或者期货交易出现重大异常波动的,期货交易所对其为维护期货交易正常秩序和市场公平,按照本法和业务规则规定履行职责造成的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存在重大过错的除外。”
第九十五条列举的情形包括“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重大技术故障、重大人为差错等突发性事件”,比第九十一条少了“发生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而这种情况也会影响期货交易正常进行或者导致期货交易出现重大异常波动,因此应当将此种情形加人第九十五条。
在法律效果上,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和第九十五条都规定,期货交易所根据其职责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置而造成损失的,期货交易所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存在重大过错的除外。这两个条款的规范意旨和法律效果都是一致的。因此,第二十一条应当援引第九十五条,而非第九十一条。
因此,建议将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发生本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导致期货交易价格出现重大异常的,期货交易场所按照业务规则可以取消交易或者调整交易价格,并及时向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公告。”
将第九十五条修改为:”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重大技术故障、重大人为差错等突发性事件、发生涉嫌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而影响期货交易正常进行时,或者期货交易出现重大异常波动的,期货交易所对其为维护期货交易正常秩序和市场公平,按照本法和业务规则规定履行职责造成的损失,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存在重大过错的除外。”
四、第二十四条
目前《草案》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一种单一的价格操纵条款的反操纵立法框架,对构成要件的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对某些操纵行为类型的表述也存在一些问题。建议对相关要件和操纵行为类型的表述进行修改,同时建立欺诈操纵与价格操纵并存的市场操纵二元规制体系。
1.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以下列手段操纵期货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据此,市场操纵的构成要件既包括交易价格,也包括交易量。但根据期货市场操纵理论,在价格操纵的路径下,操纵行为的结果要件是人为价格,而行为人的意图则是影响市场价格,因此操纵对象就应该相应地被表述为”交易价格”。与交易价格不同,交易量并不直接与行为人的利益挂钩,交易量的变动也并非行为人操纵市场所要达到的目的。对交易量的影响只是行为人为实现价格影响所运用的一种手段,[2]或者是在价格操纵认定框架之下证明行为人具备影响价格的能力的证据之一。[3]所有操纵行为都是影响或者意图影响市场价格的行为,但并非所有操纵行为都包含对市场交易量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价格操纵条款可以被作为市场操纵的兜底性条款,而交易量的变动并不包含在价格操纵条款的证明要件中的原因。因此,单纯对交易量的操纵并不构成操纵认定的决定性因素,所谓“人为交易量”也并非价格操纵的构成要件,“交易量”本身不应该被表述为价格操纵条款中与”交易价格”并列的操纵对象之一。[4]
2.第二十四条第七项规定的操纵行为类型是“为影响期货市场行情囤积现货”。该表述继承自《条例》,一般认为是对“囤积”(COrner)操纵行为的规定。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多头囤积和空头囤积。前者对应的是“多逼空”的情形,其目的是让空头不能取得现货供应来交割;后者对应的是“空逼多”的情形,其目的是通过向期货市场大量交割现货而压低期货价格。[5]“多逼空”对行为人而言需要同时在两方面取得支配性的多头头寸,一方面是将要到期的期货合约,另一方面是期货合约项下的可交割现货供应。多头操纵者将其支配性期货头寸保留到交易的最后时段,并因此获得该期货品种相当比例的未平仓合约。因为空头起初并未预计到必须交割,而多头又垄断了可用于交割的现货供应,所以其事实上处于可以同时决定合约的对冲平仓价格以及可供交割的现货商品价格的地位。[6]当交割期到来时,空头无法从市场中获取现货用于交割。为避免承担违约责任,且考虑到交割的成本和不便,空头大多会选择以多头设定的高价来对冲平仓。[7]相较而言,“空逼多”的情形较为罕见,但这种操纵手法也是能够实现的。如果空头期货交易者囤积大量现货,并在期货市场上就这些现货供应发出大量的交割通知,多头为了避免必须受领实物交割,就会开始恐慌性抛售,导致期货价格被压低。空头就可以在该低价上买人多头合约,通过对冲平仓来了结其合约义务并盈利。与此同时,现货价格也会因为期货价格而走低,空头也可以以低价买人现货用于交割而盈利。[8]可见,无论是多头囤积还是空头囤积,行为人仅仅囤积现货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持有支配性的期货头寸。[9]
此外,该项将行为人的意图表述为“为影响期货市场行情”。一般认为,“市场行情”至少包括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但是在囤积操纵中,行为人就是靠其在期现货市场中的支配性地位,以及期货合约的实物交割条款,来逼迫合约对手方以高价/低价对冲合约。因此,行为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特定的高价/低价,而完全不关心价格以外的诸如交易量等“市场行情”。因此,该项中对行为人意图的表述也是不恰当的。
3.目前,《草案》中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一种单一的价格操纵条款。在价格操纵的规制框架之下,以人为价格为核心的构成要件的证明较为困难,且因为极易受到攻击而无法成立。近年来,美国通过《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在期货市场中增加了基于欺诈的反操纵条款,确立了欺诈操纵与价格操纵并存的二元规制体系,进而大大增强了监管机构的执法能力。与价格操纵相比,欺诈操纵虽然调整范围稍窄,但证明难度更低。在法律适用上,两种反操纵条款可以择一适用,也可以同时适用而提出两个并行诉求。欺诈操纵条款通常被作为一般性的反操纵条款,而价格操纵条款则作为兜底性条款。为提升监管机构的执法能力,在我国期货市场操纵立法和执法中没有必要坚持单一的价格操纵规制框架,而应当建立欺诈操纵与价格操纵并存的二元规制体系,从而降低操纵行为的认定难度和执法成本,同时提升监管效率。在欺诈操纵的路径下,对操纵进行规制和证明的逻辑在于,行为人通过操纵性或欺骗性的手段对他人造成了误导,即欺诈。从该角度出发,操纵活动对各种市场行情要素的影响都会产生虚假信息,从而可能造成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误导。市场行情主要由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组成,但不限于这两个方面,还包括其他所有能够影响市场参与者交易决策的要素。因此,操纵活动对包括“交易价格”“交易量”在内的“市场行情”所造成的影响本身虽然并非欺诈操纵的构成要件,但却是行为人所采用的欺诈性手段和相关性要求的证据。所以说,操纵交易量其实是一种误导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手段,其背后所代表的其实是对欺诈操纵的证明要求。[10]
因此,从整体上建议将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禁止以下列手段操纵期货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期货交易价格或者期货交易量:……(七)为影响期货市场行情在期货市场建立支配性持仓的情况下囤积现货;……”
五、第二十五条
《草案》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进行期货交易的,视为内幕交易,但是能够证明没有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除外。”
如果天然橡胶期货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进行股指期货交易,显然不能被视为内幕交易。只有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才能被视为内幕交易。
该款规定应该是参考了证券内幕交易中对“利用”要件的认定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五条规定:“会议认为,监管机构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处罚人不能作出合理说明或者提供证据排除其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相关证券交易活动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内幕交易行为成立:(一)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二)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其证券交易活动与该内幕信息基本吻合;(三)因履行工作职责知悉上述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四)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并进行了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活动;(五)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
可以看到,其中的第(一)项就是如此表述的。
因此,建议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进行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的,视为内幕交易,但是能够证明没有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除外。”
六、第二十六条
《草案》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四项将“其他相关市场中的重大异常交易信息”作为列举的内幕信息之一。首先,立法技术上的问题是,如果其他相关市场中的重大异常交易信息是内幕信息,那么本市场中的重大异常交易信息为什么不是?其次,一旦被认定为内幕信息,对相关知情人就会产生“披露或戒绝交易”的义务。典型的如错单交易,如果必须向全市场披露才能继续交易的话,那么根本无法再完成对冲交易,甚至有可能迎来全市场的逼仓。因此,此种披露义务是不符合市场和交易规律的,不宜将本人的重大异常交易信息定性为内幕信息。如果在异常交易及相关反向交易中,行为人具备影响价格的意图或以欺诈手段操纵市场,可以认定其构成操纵,但不宜认定为内幕交易。至于他人的重大异常交易信息,可以定性为内幕信息(重大未公开信息)。[11]但这种情形该条第三项已经可以涵盖。
因此,建议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四项删除。
七、第四十五条
《草案》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结算参与人违约的,期货结算机构按照业务规则以结算参与人的保证金、风险准备金、结算担保金和自有资金等代为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此取得对该结算参与人的相应追偿权。”
当结算机构以结算参与人的保证金来承担违约责任时,是不应该产生追偿权的。只有以风险准备金、结算担保金和自有资金时,才能称为“代为”承担违约责任,进而产生对结算参与人的追偿权。
应当沿用类似《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表述方式:“会员在期货交易中违约的,期货交易所先以该会员的保证金承担违约责任;保证金不足的,期货交易所应当以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金代为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此取得对该会员的相应追偿权。”
因此,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应修改为:“结算参与人违约的,期货结算机构按照业务规则以结算参与人的保证金、先以该会员的保证金承担违约责任;保证金不足的,期货结算机构以风险准备金、结算担保金和自有资金等代为承担违约责任,并由此取得对该结算参与人的相应追偿权。”
八、第四十六条
《草案》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结算参与人、交割库进人破产或者清算程序的,保证金、进人交割环节的交割财产应当优先用于结算和交割。”
交割库不应出现在该款中,否则按照反面解释,交割库中未进人交割环节的财产、交割完成后剩余的财产就属于交割库的破产或者清算财产?事实上,保证金、交割财产的所有人都是结算参与人,与交割库无关,交割库只是交割财产的保管人。
因此,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应修改为:“结算参与人、交割库进人破产或者清算程序的,保证金、进人交割环节的交割财产应当优先用于结算和交割。交割库中的交割财产不属于交割库的破产或清算财产。”
九、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期货交易的交割或者行权,由期货结算机构组织进行。期货交易的交割包括实物交割、现金交割。”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采取实物交割的,期货结算机构负责组织货款与标准仓单等合约标的物权利凭证的交付。期货交易场所负责标准仓单的登记。采用标准仓单以外的单据凭证或者其他方式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场所应当明确规定交割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期货交易的实物交割在期货交易场所指定的交割库、交割港口或者其他符合期货交易场所要求的地点进行。实物交割不得限制交割总量。”
第五十条规定:“采取现金交割的,期货结算机构以交割结算价为基础,划付持仓双方的盈亏款项。”
“交割”或“行权”都是针对“合约”而言的,而非“交易”。准确的搭配是“期货交易的结算”“期货合约的交割”“期权合约的行权”。后两条另外的问题在于缺少主语。
因此,第四十八条应修改为:“期货交易、期权合约的交割或者行权,由期货结算机构组织进行。期货交易合约的交割包括实物交割、现金交割。”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应修改为:“合约采取实物交割方式的,期货结算机构负责组织货款与标准仓单等合约标的物权利凭证的交付。期货交易场所负责标准仓单的登记。采用标准仓单以外的单据凭证或者其他方式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场所应当明确规定交割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期货交易合约的实物交割在期货交易场所指定的交割库、交割港口或者其他符合期货交易场所要求的地点进行。实物交割不得限制交割总量。”
第五十条规定:“合约采取现金交割方式的,期货结算机构以交割结算价为基础,划付持仓双方的盈亏款项。”
十、第三章标题与位置
《草案》第三章标题为“其他衍生品交易”,但是其中的第三十九条是有关结算的,因此建议将第三章标题改为“其他衍生品交易与结算”。并且将第三章与第四章的位置对调。第三十九条中有参照后面的第四十六条规定执行的规则,对调后,被参照的条文先出现,在立法逻辑上也更恰当。
十一、第六十八条
《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期货公司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期货自营业务。”在《草案》第六十八条中,这一规定被删除了,同时规定:“期货公司经过核准可以从事下列期货业务:(一)期货经纪;(二)期货投资咨询;(三)期货做市交易;(四)其他期货业务。”鉴于《条例》对期货自营业务的禁止性规定,如果《期货法》的立场是期货公司经核准可以从事期货自营业务,那么建议在第六十八条中予以明确。毕竟列举了不代表马上可以从事,还需要主管机关核准。
十二、第七十八条
《草案》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责令负有责任的股东转让股权,限制负有责任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不能既责令负有责任的股东转让股权,又限制其行使股东权利。
因此,建议将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修改为:”责令负有责任的股东转让股权,或限制负有责任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十三、第九十八条
《草案》第九十八条规定:“期货结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是结算参与人共同对手方,进行净额结算,为期货交易提供集中履约保障。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终止净额结算行为,不因结算参与人依法进人破产程序而无效或者撤销。”
该条第一款明确了期货结算机构中央对手方的地位,但是对结算机构介人合约的时点以及相关法律关系未予明确,容易引起适用上的争议。国际清算银行(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联合发布的《对中央对手方的建议》指出:“在大多数法域内,使得中央对手方成为对手方的法律概念是合约更替或公开要约。通过合约更替,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原合约被两份新合约取代而消灭,其中一份产生于中央对手方与买方之间,另一份产生于中央对手方与卖方之间。在公开要约制度下,中央对手方在买卖双方就交易条款达成一致时立即自动地介人该项交易。如果所有预先约定的条件得到实现,公开要约制度下的买卖双方之间自始不存在合约关系。如果法律体系支持所采用的方式,无论合约更替还是公开要约,都可以在使中央对手方负有效结算义务方面,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法律确定性。”[12]
在期货交易撮合后,即会提交给结算机构进行结算。因此,可以将期货结算开始的时点设定为结算机构介人合约关系成为中央对手方的时间。这样也能涵盖场外衍生品交易达成后提交给结算机构进行中央对手方结算的情形。另外,第二款有一些语言表述上的问题。
因此,建议在条文表述上将第九十八条修改为:
“期货结算机构作为中央对手方,是结算参与人共同对手方,进行净额结算,在结算开始时介人期货合约关系,成为买方的卖方、卖方的买方,为期货交易提供集中履约保障。
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终止净额结算行为,不因结算参与人依法进人破产程序而无效或者被撤销。”
十四、第一百一十四条
《草案》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期货经营机构、期货服务机构等从事期货相关业务的机构应当加人期货业协会。”
根据第一百零六条,期货服务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期货保证金存管机构、交割库、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信息技术服务机构。其中,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的主营业务一般并非期货业务,没有必要要求其加人期货业协会。《证券法》也没有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加人证券业协会。建议直接采用列举的方式,将与期货市场直接相关的应当加人期货业协会的主体列举出来。
因此,建议将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期货经营机构、期货服务机构期货保证金存管机构、交割库、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期货市场信息技术服务机构等从事期货相关业务的机构应当加人期货业协会。”
[*]钟维,中国人民大学营商环境跨学科交叉平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营商环境跨学科交叉平台的支持。
[1]参见钟维:《期货交易双层标的法律结构论》,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4期。
[2]参见上海期货交易所《“期货法”立法研究》课题组编著:《“期货法”立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第705页。
[3]参见程红星、王超:《美国期货市场操纵行为认定研究》,载曹越主编:《期货及衍生品法律评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页。
[4]参见钟维:《欺诈理论与期货市场操纵二元规制体系》,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
[5]See Philip McBride Johnson, Commodity Market Manipulation,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Vol. 38, No. 3 (1981), p.731.
[6]See Ralph T. Byrd, “No Squeezing, No Cornering: Some Rules for Commodity Exchanges”, Hofstra Law Review, Vol. 7, No.4 (1979), p. 930.
[7]See William D. Harrington, The Manipulation of Commodity Futures Prices, 55 St. John’s Law review 240 (1981), p. 250.
[8] See William D. Harrington, The Manipulation of Commodity Futures Prices, 55 St. John’s Law review 240 (1981), pp. 249 - 251; Philip McBride Johnson, Commodity Market Manipulation, 38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725 (1981), p. 731.
[9]参见钟维:《跨市场操纵的行为模式与法律规制》,载《法学家》2018年第3期,第115-116,119页。
[10]参见钟维:《欺诈理论与期货市场操纵二元规制体系》,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3期。
[11]参见钟维:《期货市场内幕交易:理论阐释与比较法分析——兼论我国期货法之内幕交易制度的构建》,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2]Committee 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Recommendations for Central Counterparties, p. 13, 资料来源:https://www.bis.org/cpmi/publ/d64.pdf,2021年9月20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