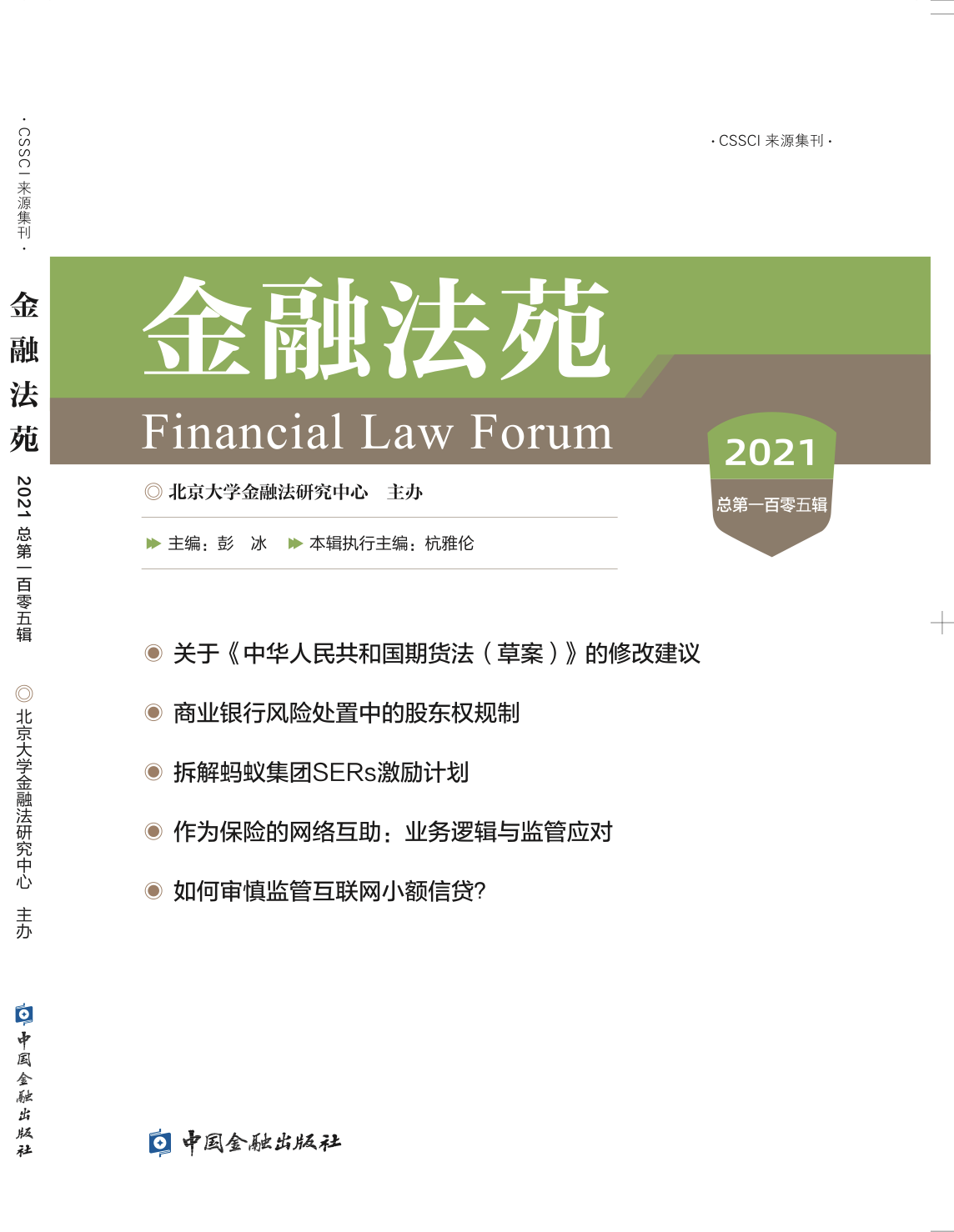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作者】杨骐玮,北京大学法学院2020级经济法学硕士。
摘要:互联网小额信贷通过联合贷或者助贷模式进行横向扩张,也通过资产证券化扩大融资规模,监管者需要关注其业务扩张模式所带来的风险防范需求。联合贷与助贷扩张模式的核心隐患为蕴含于银行与小额贷款公司合作关系中的代理成本问题。对此,应当强调银行对核心风控的独立把握,以及通过提高合作方的风险承担比例以抑制合作方的道德风险,即遵循以商业银行安全为导向的审慎监管思路。在以自营贷款做资产证券化的扩张路径中,考虑到资产证券化固有的风险转移逻辑对削弱授信审查标准的投机行为的激励,以及网络小额信贷在完整经济周期的表现尚未验明,为防范宏观风险,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证券化融资规模进行限制并进而控制信贷总量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防范还应着眼于底层资产质量的保证以及市场入口处的把关。
关键词:互联网小额信贷 审慎监管 助贷与联合贷 资产证券化 蚂蚁花呗
一、问题的提出
在借贷领域,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手段比如获取客户的信用历史、收入信息或合格抵押品,[1] 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稀缺方拒之门外,而金融科技的助推使得信贷扩张或下沉大有破竹之势。对于缺乏信用记录或抵押品的长尾客户,尤其是个人和中小企业,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大量替代性数据[2]来改善这些客户的信用评估,从而做出授信决定。[3] 非银行金融科技企业显著提高了小额信贷的可得性。在中国金融抑制的大背景下,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更是通过互联网小额信贷[4]异军突起,低门槛、易得且便利的信贷提供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普惠金融的理念。
互联网小额信贷的规模攀升得益于合作银行的资金提供与证券化融资模式的助力,然而,对银行信贷业务的巨大牵涉与跨市场的风险传递引发了监管部门的忧虑。于是《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86号文”)、《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24号文”)纷至沓来。其中,《暂行办法》与《24号文》是专门适用于商业银行的规范性文件,处理银行与外部主体在互联网小额信贷业务上的合作应如何开展的问题。《86号文》与《征求意见稿》针对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这一类主体,后者更准确而言,其适用主体为从事互联网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分别运营“花呗”与“借呗”两大拳头产品的蚂蚁集团全资控股的小额贷款公司自然落入其射程范围之内,于是,该文件甫一公布便直接导致了蚂蚁集团的暂缓上市。[5]
一系列监管规则的出台反映了监管机构对互联网贷款业务治理的高度重视。互联网小额信贷之所以如此受到监管关注,是因为在与银行的合作模式中,小额贷款公司做的几乎是只赚不赔的生意,其或收取技术服务费,或收取远超其所承担风险比例或出资比例的利息分成,而合作银行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出资与风险,[6] 授信审查不严造成的不合理风险传导恰如“此之蜜糖,彼之砒霜”,由此,需要强调以商业银行安全为导向的审慎监管。与此同时,小额贷款公司以其放贷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通过证券化进行融资,此种模式的外溢性与风险根源也需要进行仔细分析,进而选择合理有效的应对方法。
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对互联网小额信贷的两类主要扩张模式进行介绍,再着重考察助贷和联合贷模式的风险,并对目前的监管规则加以分析评述,进而寻找正确的治理端口与监管介入的路径;第三部分侧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外部融途径,尤其是资产证券化的规制进行分析,从而判断监管思路的合理性并提出更理想的监管进路;第四部分为对前文的简要总结。
二、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基于银行的风险承担
微观审慎监管着眼于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健,宏观审慎监管旨在削减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以防范系统性风险,[7] 总体而言,审慎监管的介入是基于风险防范与控制的需要。互联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呈现出了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原点的横纵扩张之势,具体来讲,由于自有资金规模对放贷规模与盈利水平的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在横向上寻求与资金雄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联合贷与助贷业务,同时在纵向上通过资产证券化从二级市场融资,用以继续放贷。可见,并不能将小额贷款公司与互联网小额信贷业务等同,小额贷款公司自身并不具有像商业银行一样的重要地位与风险防范和审慎监管的需求,而互联网小额信贷业务由于参与主体的复杂性和跨越至资本市场的影响力,需要监管者仔细评估其各种业务模式的风险,并以此为依据决定审慎监管是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
(一)互联网小贷的扩张进路:以“花呗”为例
自蚂蚁集团筹划上市以来,以“花呗”和“借呗”为代表的互联网小额消费信贷业务一直备受瞩目,二者分别由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微小贷”)和蚂蚁商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运营。“花呗”与“借呗”相比,由于对客户的资质要求更低而收获了更大的用户基数,成为了广大消费者群体更为熟悉的一款产品。故而,本文以“花呗”为例来简要介绍上述网络小额信贷的横纵扩张进路。
首先是联合贷与助贷模式。根据最新的《花呗服务协议》,[8] 蚂蚁[9]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提供授信及相关服务,具体参考《花呗·消费信贷授信合同》(《花呗服务协议》附件中的模版合同一)可看到,多个授信主体在消费场景下共同向客户授信,而授信资金直接支付给交易对手,此即联合贷模式;另外,在非联合授信的情况下,单个授信主体不一定是小微小贷,也可能仅仅是合作金融机构,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助贷模式。联合贷与助贷是《征求意见稿》更为关心的展业方式。[10]
其次是跨市场拓展融资来源的模式,体现为自营贷款做资产证券化,即在小微小贷在作为授信主体的同时,亦作为原始权益人将保留在自身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打包做证券化来融资从而实现资金周转。《86号文》最先对这一模式的融资规模加以限制。[11] 此外,跨市场融资还包括商业保理公司购买应收账款再做证券化的途径,但此类模式事实上逸出了监管的视野范畴。根据《个人保理付款服务合同》(《花呗服务协议》附件中的模版合同二),蚂蚁集团全资子公司商融保理作为授信主体,在客户购买商品或服务时,根据花呗额度和交易金额,购买交易对手对客户的应收账款债权,随后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将该笔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来融资。不过,由于《86号文》与《征求意见稿》的规范对象仅限于小额贷款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的同质行为并未落入其规制范围。
以下首先对涉及商业银行参与的联合贷与助贷模式展开分析。
(二)对助贷与联合贷模式的风险识别
助贷可简单概括为“导流 + 初筛”,蚂蚁向合作金融机构提供蚂蚁风控下初筛的结果,再由合作金融机构自行决策和授信,蚂蚁赚取技术服务费而不承担任何信贷坏账的损失。对于缺乏信用记录、贷款经验的下沉群体,蚂蚁智信或小微小贷借助“芝麻信用”[12] 对其做出了认可并提交至合作金融机构的决定。由于蚂蚁已具备足够的数据和经验支持,其评估结果的可信度较高,再加上合作金融机构自身难以获得其他有意义的数据并作出独立判断,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信任蚂蚁的信用评估结果。在联合贷模式中,基于同样的原因,合作金融机构亦难以独立完成授信审查与风控,并依赖和信任蚂蚁的评估结果。与此同时,蚂蚁在导流的基础上仅需提供极低比例的授信资金,[13] 却能够从利息中分成30%-40%,还要收取技术服务费,[14]并且绝大部分授信所形成的资产都处于银行等合作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蚂蚁几乎不承担坏账损失。
不论是助贷还是联合贷,其合作模式与收益分配结构均蕴涵着较大的道德风险或者较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对于蚂蚁而言,低成本、低风险、较高回报的合作模式很可能激励其为增长收益而盲目降低授信审核标准,而信贷难以收回的风险以及实际损失,绝大部分都落到了银行的头上。存在这种严重道德风险的症结在于银行在授信审查及风控上对蚂蚁的较大依赖。
(三)风险防范:以银行为核心治理端口
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以银行为核心治理端口。首先应明令银行不得将授信审查与核心风控外包,并且严格把控与第三方的合作的规模和限度。由此出现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独立开展授信审批等核心风控环节的要求,[15] 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有关强化合作机构集中度管理、实施总量控制和限额管理的规定。[16] 合作规模的限制实则是对风险总量的控制,但无助于消解联合贷与助贷的合作模式所内生的代理成本问题。所以,另一方面,需要在银行与第三方合作的每笔业务中,通过风险分配、风险承担的强制性规则,削弱第三方的道德风险。比如可以要求小额贷款公司提高其在授信资金中的出资比例而承担更大的损失风险,从而激励其在授信审查标准的制定与执行上更为严格谨慎,《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与《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对联合贷模式中小额贷款公司等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的规定就旨在实现这一目的。
不过,本文认为,该规则更适合出现在以规范商业银行业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当中,而不宜保留在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主要规范对象的《征求意见稿》内。不仅是因为规则的不必要重复,更重要的是,规则的位置会传递出监管机构对风险治理端口与“归罪点”的认识,而错位很可能造成人们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不必要误会与有关风险来源认识的混淆。从以上规则的落实来讲,出资比例、集中度管理、限额管理等刚性指标极为明确且便于执行,而对于银行核心风控不得外包这一较为原则性要求的真正落实,有赖于银行自身数据获取与处理能力的提升、风控模型的改革与优化,以及外部征信系统作用的充分发挥。
总的来说,上述规范的出发点在于确保商业银行自身的安全稳健经营与有效风险防范,更侧重微观审慎目标的实现。其所处理的问题本质是银行与第三方合作的边界,尤其是二者在关于授信的权利、义务与风险上的分配界限,防止银行“被迫”[17]转变为“狭窄的银行”而仅限于资助由BigTech发起和承销的贷款。[18]
三、审慎监管的错位:外部融资限制
相比于可以使用自身所吸收的存款放贷的商业银行,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非存款类放贷组织获取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对于股东借款、银行借款、发行债券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外部融资渠道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而资产证券化相比于其他三种融资模式,向公开市场的信息披露程度更高,并且具有独特的风险转移逻辑,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证券化融资,具体来讲是以保留在自身资产负债表上的信贷资产作为底层资产,进行证券化处理,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从而募集资金,[19] 该笔融资可用于继续放贷并将由此形成的信贷资产再次做证券化。通过此种循环往复,自营贷款主体仅需极低的初始成本就能“撬动”巨大的信贷规模。《86号文》对通过这种模式融资的体量加以限制,要求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四倍,同时还规定了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融资形式融入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一倍;《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针对“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重申了这一要求。
(一)监管机构的可能考量
限制资产证券化融资总量的根本目的在于对信贷规模进行控制。设置证券化融资规模红线、立足于总量控制的规则显然是遵循了审慎监管的思路。那么,此种审慎监管是基于何种风险、侧重点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以及所采用的手段合理与否呢?
首先,自营贷款资产证券化对于非存款类放贷组织个体而言,几乎不存在风险。小额贷款公司等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而资产证券化对其而言,是一种将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转移至外部并降低企业负债、促使资金快速回流的融资工具。可见,在个体层面,不存在对此种融资模式加以审慎监管的需求。而且,域外对于非存款类的放贷机构,亦无审慎监管的惯例。例如美国,对于持牌放贷机构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州一级别,包括准入制度和以信息披露而非利率管制为核心消费者保护制度。具体如加州,根据《加利福尼亚金融法》,“任何人如未获得专员许可,不得从事金融贷款人或经纪人的业务”,[20] 持牌贷款人能够获得州高利贷规则的适用豁免,突破本州的法定利率上限,从而收取比民间借贷更高的利率。[21] 但与此同时,持牌贷款人受到更为严格的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约束,比如,不得就贷款的条款、条件向借款人做出虚假或误导性陈述,并且广播、印刷、出版等各种形式的广告都不得违背这一要求,而且对于广告的投放处与内容有诸多限制。[22] 除了各州自己的立法,在联邦层面还存在更为广泛适用的信贷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意图保证信贷条款透明度与有意义披露的《诚实信贷法》、[23] 反歧视的《公平信贷机会法》以及维护消费者知情权与隐私权益的《公平信用报告法》。总之,对于放贷组织,不仅不存在审慎监管的实际需求,而且在实践中也难觅对其进行审慎监管的制度。
其次,限制证券化融资规模,并将此效应传导至信贷总量控制的思路体现的是监管机构有关宏观审慎的考量。
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在于,网络小额信贷的承销准确性与贷款表现尚未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的检验,诸多有关网络小贷的不确定性可能在经历了整个经济周期的衰退后才会得到澄清。在此情况下,采取保守的总量控制规则与逆周期调节方法起码能确保未来不会产生较严重的风险。在不利的经济条件下,贷款需求和资金可得性可能会下降,此时,网络小贷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才能得到进一步揭示。单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失败本身并不是问题,不具有竞争力或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的失败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然而,当小额贷款公司普遍倒闭,尤其是当这些放贷组织已经成长到了可以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大量信贷的程度,其倒闭就可能会导致信贷的急剧收缩,进而造成实体经济严重缺乏资金。并且在资产证券化的情况下,放贷组织除了是原始权益人之外,通常还会承担资产服务机构的角色,负责后续的催收等环节,其倒闭也可能会影响向证券投资者支付的现金流。[24]
另一层原因是对资产证券化的“发起-转移”(originate-to-sell/distribute)模式固有风险的担忧。在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 ABS)模式下,放贷组织或原始权益人将信贷资产进行打包和真实出售,完成了与信贷资产风险的隔绝,投资者在认购相应份额后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仅来自于基础资产池的信用质量及其支付特征,[25] 所以基础资产的质量是决定投资者回报的最关键因素。由于放贷组织并不持有其发放出去的贷款及承担相应风险,而是通过发起证券化和服务费来赚取大部分收益,这很可能造成对授信审查松懈、承销标准薄弱的激励。[26] 尽管在目前的ABS中,原始权益人大多会遵照5%的比例进行风险自留,[27] 但是这一风险共担(skin in the game)的手段究竟能否抑制放贷组织的道德风险,并不存在极为明确的答案。因此,在无法确切根除ABS模式固有风险的情况下,转求通过限制信贷总量与ABS规模,防止出现大面积证券化产品违约、投资者损失与市场震荡的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28]
(二)对“外部融资限制规则”的疑惑
本文承认上述宏观审慎考虑的合理性以及体量控制对宏观风险防范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86号文》与《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中有关对外融资限制的条款,尤其是“证券化融资不得超过四倍净资产”规定的认可。
该规定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逻辑上的混乱。股东借款、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都是在融资的同时会增加企业负债的工具,而资产证券化却不会造成企业负债的增加。将企业内部增杠杆和降杠杆的工具混为一谈,并统一适用以净资产为标尺的倍数限制的规则,首先在表面上就较为凌乱,而且存在不合理叠加多重监管目标的问题。此种将资产证券化融资与其他融资合并计算并统一适用倍数限制的混乱,实际上是对《整顿现金贷通知》中证券化融资并表计算的规定的沿袭。[29] 并表计算或将资产证券化与其他融资方式放在一起讨论并非毫无根据,监管的可能考量在于,实践中,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在明面上将信贷资产真实出售,但事实上还提供隐性担保来为自己的信贷资产质量做背书,即没有实现风险的真实转移,面对此类情形,并表计算不无道理。但是,一刀切的规则会造成对底层资产质量较高且做到了真实出售、风险转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误杀”,而《86号文》和《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是“一刀切”思路的延续。除此之外,《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所传达出的多重监管目标也令人困惑。比如,规定证券化融资的倍数上限,根本意旨应该是控制信贷规模;而向银行借款不得超过净资产一倍的规定,可能体现的是另一种目标,即确保商业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监管机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资产质量较为担忧,为防止其因不具备充足的现金回流而难以向银行偿付、影响到银行的安全稳健经营,而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的借款应限制在自身净资产的一倍以内。然而,银行在对外贷款上已经受到了一系列规则的约束,比如《商业银行法》中有关贷款集中度的规定,[30] 如果认为现有规则在应对网络小额信贷上存在不足,也应该从银行端加以控制,要求银行在评估小额贷款公司的偿付能力与确定贷款数额上遵循更严格和具体的规则,而不适合从原则上不应受到审慎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端设定规则。简而言之,《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表现出了逻辑的混乱、审慎监管的错位与反应过度。
其次,即使该规则以限制整体信贷规模为核心目标,然而由于规范对象的不周延,很可能导致这一目标的落空。如上所述,商业保理公司通过购买应收账款进而做证券化也是花呗拓展融资来源、放大信贷规模的主要途径,而且类似模式还被不少其他消费信贷的经营主体所采纳。[31] 商业保理牌照为此类玩家提供了规避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的逃逸空间,笔者认为,这并非是监管机构所乐于见到的现象,不过目前的规则确实对此无能为力。
再者,该规定又一次体现出了我国监管机构“急用先行、问题导向”的处事风格,虽然其落实会使得信贷资产的总量、证券化融资的规模与市场风险较快地降落到监管所认为的最佳水平,然而,这种方法或许无助于从源头上防范宏观风险。滋生宏观风险的核心问题在于基础信贷资产质量不良及向二级市场与投资者的不合理风险转移。对此,应诉诸于最基本的两层入口把关。
第一层是对于信贷资产质量的把控,尤其应要求从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放贷组织在授信审查上遵守更严格的标准。传统的放贷组织以股东资金放贷,损失自担,因此对于其放贷标准没有必要进行监管。然而,在资产证券化模式下,信贷风险最终由投资者承担,监管必要性由此显现,因此,对于资产证券化的信贷资产应有一定的标准要求。[32] 具体要求比如,放贷组织仔细进行主体核验认证并确认贷款具有较为明确的用途或使用方向;重视借款人的其他债务负担情况以对其偿还能力和风险作出合理评估;在信用评估时所使用的替代性数据应限于与信用有关的信息,而不得根据其他无关信息比如学历作出授信决定;向监管机构披露授信决策所使用的数据类型及测算模型以供审查监督;向征信机构报送用户信贷产品的使用情况并与之形成互利互惠的关系,合力防范借款人的共债风险。不过,需要认识到,这些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具体要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其还是无法解决金融科技贷款的严重不透明性问题。有学者认为,机器学习、算法驱动的过程会产生黑箱效应,不论是放贷者还是投资者都缺乏对估值模型固有局限性、短期历史数据风险以及信贷资产基本质量的理解。机器或者智能承销与证券化的结合会加剧对实际风险的掩盖,真正的风险比以前次贷危机的MBS更加不为人知,甚至是不可知的。[33] 尽管如此,依然不能忽视在信贷获取入口处的把关要求对于信贷资产质量提高的积极意义。
第二层是在信贷资产向二级市场的登陆入口处把关,需要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与市场看门人职能的有效发挥,从而实现充分的风险揭示和预警。目前有关基础资产池、现金流来源和流动性安排的风险揭示仍然不够充分,给量化风险制造了障碍。[34] 同时,市场看门人机制也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尤其是评级机构的看门人职能发挥得并不尽如人意。评级机构在扩大网络小额信贷ABS投资者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5] 由于牵系着众多投资者的信任,评级公司所传递出的清晰直观的价值判断,对投资者的决策构成了巨大的激励。然而,由于监管机构对评级机构所采用的数据和模型没有强制性披露要求,因此评级方法缺乏透明度,这进一步导致监管机构与投资者对评级机构专业能力与是否尽职的判断无能。此外,由于我国以主体为依据进行ABS规则适用的划分,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其他放贷组织在信贷ABS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对称监管问题,[36] 这一点在评级制度上亦有体现。例如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ABS在试点之初就采用“双评级”制度,并对评级准入资格、管理规则等做出详细规定;但根据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规以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则,非金融机构的信贷ABS并不存在“双评级”的要求,评级体系的差异对评级结果的可信度造成了一定影响。[37] 尽管解决市场割裂与规则不对称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功,但是目前在交易所的层面,在评级制度的严格化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评级机构职能充分发挥、有关基础资产质量和现金流来源的风险得到充分披露的情况下,具有特定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根据相关信息作出投资决策,这是一种以买者自负为原则、量力而行的合理风险承担,不需要监管的额外介入。[38]
虽然上述两个基本层面把关的完全落实是一种十分理想化的状态,但这应当是监管所追求的长远目标。信贷资产的大规模不良以及向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不合理风险输送不是简单的倍数限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观察域外的立法与监管现状,也并未发现杠杆率规则在持牌放贷机构对外融资规模上的运用,即使是次贷危机后的美国也未设置明确的杠杆指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在州和联邦层面对于持牌放贷人的规制皆以消费者保护为导向。再看欧盟,尽管部分国家如法国、德国、爱尔兰及意大利对非银行贷方(non-bank lenders)存在对外借款或者总资产相对净资产的比率限制,[39] 但是准确来讲,这些限制的针对对象是发起贷款的“另类投资基金”(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AIF),其所遵循的规则为《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令》(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AIFMD)。[40] 而此种基金形式的非银行贷方,是否与大部分国家的以公司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放贷机构运作原理类似,并且进而在相关规则(比如杠杆率)上能够作出类似设计,还有待深入考察,不能盲目进行制度移植。总之,对于非存款放贷组织的对外融资规模强加限制确非国际上的常见做法。
在我国,由于网络小额信贷的迅速扩张,风险厌恶与敏感型的监管机构考虑到网络小贷基础资产质量尚未经完整经济周期检验,而对其表现出谨慎、怀疑与担忧的看法,并进一步诉诸于总量控制的规则,并非毫无道理。只是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不能因为在对外融资及信贷规模控制上取得的成果而放弃了上述两个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尽管对于网络小额信贷在完整经济周期中的表现还不能完全明确,但是应当进行持续的评估,审视是否应当设置杠杆率红线与限制ABS融资规模,或者具体的杠杆率与倍数是否合理。
(三)监管工具的“时效性”
以上是从监管逻辑合理构造的角度出发对外部融资限制规则加以分析,而从规则的具体落实效果来看,外部融资倍数等审慎监管指标[41]还存在着“时效”的局限性。因为对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严厉约束会刺激其向杠杆倍数更高、资本金要求更低、融资成本更低、享有同业拆借便利的消费金融公司转型,[42] 而其一旦将业务转移至消费金融公司,原先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规模限制和最低资本金等规则便无法继续适用。[43] 这并非臆测,现实中的确出现了如此动向,根据蚂蚁集团在港交所的公告,“花呗”、“借呗”将被纳入消费金融公司。[44] 欠缺理性、过度审慎、意在精准打击却又不存在完善的规制框架为依托的监管工具很可能自一出生便注定了被规避和遗弃的命运。
综上观之,按照审慎监管的思路,针对从事互联网小额信贷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施加严格的对外融资规模限制与极高的资本金要求,不仅逻辑不顺,而且存在沦为具文的可能。事实上,对于互联网小额信贷,监管更应侧重消费者保护方面,要求放贷组织做到在信息披露上的全面透明和在催收行为上的规范。[45] 以美国为例,除了各州单独立法外,联邦一级还存在着《诚实信贷法》、《公平信贷机会法》和《公平信用报告法》以促进消费者对贷款产品的信息有全面清晰的了解,以及公平地获得信贷。由此,在联邦和州两层形成了以消费者保护为核心的规范体系。总而言之,消费者保护才是对放贷组织的贷款业务加以监管的底层逻辑与核心使命,这并不会因为贷款业务被贴上互联网的标签而改变。
四、结论
联合贷、助贷与自营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是互联网小额信贷大规模扩张的利器。对这两种扩张路径的规制应遵循风险溯源与对症下药的逻辑,即需要找到风险防范和控制的正确治理端口。
在联合贷和助贷业务中,并不存在小额贷款公司故意向银行转移风险的问题,小额贷款公司不是造成风险的原罪。是否与小额贷款公司等第三方合作以及合作规模控制在多大都是银行自行决策的,因此,在风险治理上,银行理应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和承担更大的责任。故而,需要以银行为规范主体,促使其提高在授信审查等核心风控上的能力和独立性,并妥善应对联合贷与助贷模式本身隐藏的代理成本问题,要求合作持牌贷款机构提高风险负担的比例以抑制合作方的道德风险,从而实现保障自身安全的审慎监管目标。
在自营贷款资产证券化模式中,小额贷款公司等放贷组织以极少的资金就撬动了极大的信贷规模,并从中获利不断,这违背了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朴素观念。并且,ABS的风险转移特征可能加剧小额贷款公司的投机心理与授信审查标准松懈的道德风险。在无法完全克服ABS模式的固有风险、以及并不确切了解网络小额信贷资产在完整经济周期的表现的情况下,通过对融资体量加以控制,并以此进而调节信贷资产总量,将总体风险控制在监管机构所认为的适当可控的水平,似乎成为了顺理成章的选择。然而,表面上的顺理成章无法掩盖此种监管手段的底层逻辑缺陷。因为ABS风险爆发的根源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底层信贷资产的质量存在问题,而总量控制的审慎监管工具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对此要诉诸于更为长效的机制,包括通过完善授信审查机制以对信贷资产的质量进行把控,以及在信贷资产向二级市场登陆的入口处把关,通过信息披露机制与市场看门人角色有效发挥以向投资者充分揭露ABS的各种风险。
尽管本文对监管规则的分析和探讨较多,但与此同时,也在试图厘清对于互联网小额信贷的监管逻辑。总体而言,有关联合贷和助贷规则的出台是落实对商业银行进行审慎监管的必然要求,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设置外部融资倍数限制的规则,正如上所述,还存在商榷空间。然而,监管思路的稍微厘清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监管问题,并且也不存在能够一蹴而就的制度设计或者使其他问题全部迎刃而解的理想突破点。小到可以考察商业保理牌照是否异化为规避对放贷组织监管的套利工具,大到需要继续分析开展互联网信贷业务的不同类型放贷组织是否适合或需要差异化监管、[46] 互联网信贷的央地监管权如何配置或者说如何应对互联网无边界特性对以地域为依据的管辖权划分带来的挑战、[47] 以及由于市场条块分割带来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不一致监管问题如何解决,甚至在科技巨头向金融领域全方位出手布局的背景下,思考还可延伸至有关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的政策导向、规制目标与思路设计。这些问题还需另文讨论。
注释:
[1] See Stephen G. Cecchetti & Kermit L. Schoenholtz, Big Tech, Fintech, and the Future of Credit, Money Banking, December 21, 2020.
[2] See Cheryl R. Cooper, Alternative Data in Financial Servic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IF11630, 2020.
[3] See Lenore Palladino, Small Business Fintech Lending: The Need for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Fordham Journal of Corporate and Financial Law, Vol.24:1, p.84-85 (2018).
[4] 我国的互联网小额信贷与美国Marketplace Lending(或可译为“市场化借贷”)较为相似,二者都具备小额、短期、无担保、客户为个人或者中小企业以及依赖在线平台进行几乎是全自动化和算法化的承销等特征。See David W. Perkins, Marketplace Lending: Fintech in Consumer and Small-Business Lending,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4614, 2018. Also Se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Marketplace Lending, 2015.
[5]参见锦绣江山如画:《蚂蚁集团暂缓上市背后:网络小贷新规究竟有多大影响》,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30447814_120833323。
[6] 参见吴红毓然、胡越、张宇哲:《网络小贷新规降临》,载财新网,https://weekly.caixin.com/2020-11-07/101624251.html。
[7] 此外还应在风险出现后阻止系统性冲击的传递并减轻其影响。See Steven L Schwarcz, Regulating Financial Change: A Functional Approach,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 100: 4, pp.1441-1494 (2016). Also see Hockett, Robert C., Implementing Macroprudential Finance-Oversight Policy: Legal Considerations (October 14, 201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340316.
[8] 订立协议的主体为客户与蚂蚁智信(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智信”),而非如从前与小微小贷、商融(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融保理”)以及与小微小贷合作为客户提供授信服务的金融机构共同签订服务合同。对于缔约主体的变化,蚂蚁集团的回应是,自2018年5月花呗宣布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以来,花呗已从单一的产品升级为开放的产品平台,而蚂蚁智信提供了花呗平台的技术和运营服务,在花呗平台上,小微小贷与其他数十家金融机构共同为用户提供服务,参见https://www.longfajr.com/info/132972.html。不过,尽管缔约主体与合同条款有所变动,业务模式并无实质变化。
[9] 由于参与花呗业务的蚂蚁科技集团子公司较多,比如小微小贷、蚂蚁智信、芝麻信用等,共同提供花呗的相关服务,所以此处不展开进行区分,直接使用“蚂蚁”一词来指代相关主体,下文直接使用该词同理。
[10] 参见《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
[11] 参见《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86号)。
[12] 开通花呗,不光意味着签订了《花呗服务协议》,同时还与芝麻信用服务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芝麻信用服务合同》。芝麻信用在采集数据的同时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
[13] 参见吴红毓然、胡越:《2万亿联合贷款挑战》,载财新网,https://weekly.caixin.com/2019-10-25/101475419.html,访问日期:2021年3月17日。
[14] 另一说法是不分利润,仅按技术服务费提成30%,参见前注6,吴红毓然、胡越、张宇哲文。
[15] 在Marketplace Lending中,美国货币监理署亦十分注重市场化贷方与银行的关系,强调银行不得将核心合规性和风险管理责任外包给市场化贷方。See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Third-Party Relationships: Supplemental Examination Procedures, OCC Bulletin 2017-7, Jan. 24, 2017. Also see Jacob Gregory Shulman, Regulating Online Marketplace Lending: To Be a Bank or Not to Be a Bank, Rutgers Computer and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44:1, pp.163-[ii] (2018).
[16] 关于银行核心风控不得外包的要求参见《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三条。关于合作机构集中度、总量控制和限额管理的规定,参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第三条、第四条。
[17] “被迫”事实上也有“主动”的成分在。由于客户信用信息的贫乏以及银行获取并处理替代性数据能力的有限,银行自身在小额贷款的承销和服务上成本较高,并且收益也不可观,所以对于客流匮乏、数据获取和处理能力较差的银行,与BigTech等平台或小额贷款公司的合作成为了一种扩大业务规模、扩充收入来源、降低业务成本的支配性策略。
[18] See Jorge Padilla, Big Tech “Bank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Regulation (April 20, 202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580888. 该文还提到,从80年代和90年代的储贷危机(S&L)到大萧条的金融崩溃,再一次证明发起与提供资金(origination and funding)之间的分离是有问题的,代理模式下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而且BigTech平台进入零售银行业虽然可能短期内会刺激竞争,但从长远来看也可能会增加金融动荡并导致信贷市场更加集中。
[19] 不同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证券化适用《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主体的证券化适用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相关规定,根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企业资产证券化应向不超过二百人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20] California Financing Law, Division 9 of the California Financing Code, Article 3. Licensing, (a) No person shall engage in the business of a finance lender or broker without obtaining a license from the commissioner,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Text.xhtml?lawCode=FIN&division=9.&title=&part=&chapter=1.&article=3, accessed on March 17, 2021.
[21] 加利福尼亚州的放贷人许可证为被许可人提供了《加利福尼亚宪法》高利率条款的豁免,https://dfpi.ca.gov/california-financing-law/california-financing-law-about/。再如纽约州,根据纽约州《银行法》第340条,持牌放贷人能够收取比法定利率上限更高的利率,而非持牌放贷人不得突破该法定利率上限,https://nationwidelicensingsystem.org/slr/Pages/DynamicLicenses.aspx?StateID=ny, https://www1.nyc.gov/nycbusiness/description/licensed-lender。美国各州在Marketplace Lending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对有关持牌放贷人法规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相关动态参见 Robert Savoie & Philip Hoffman, Marketplace Lending and Fintech: The States Object, Business Lawyer, Vol.73:2, pp. 509-516 (2018).
[22] California Financing Law, Division 9 of the California Financing Code, Article 4 Regulations,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_displayText.xhtml?lawCode=FIN&division=9.&title=&part=&chapter=1.&article=4, accessed on March 17, 2021.
[23] Truth in Lending Act, https://files.consumerfinance.gov/f/201503_cfpb_truth-in-lending-act.pdf. 不过,《诚实信贷法》的保护对象为个人消费者,而不包括中小企业。在Marketplace Lending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于中小企业的保护也在被日益强调,因为中小企业与消费者在小额信贷的场景下区别往往有限,二者在信息洞察及分析上皆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共同适用“消费者保护”的逻辑。有学者指出,企业往往比消费者更成熟,商业信贷不需要像消费信贷那样受到监管,这样的认识存在偏见。商业信贷不受《诚实信贷法》(Truth in Lending Act)披露规则的约束,而透明度至关重要,需要制定普遍的规则,加强借款人保护从而为小企业借款人提供相应保护。See Karen Gordon Mills & Brayden McCarthy, The State of Small Business Lend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7-402, 2016. Also see supra note 3.
[24] See supra note 4, David W. Perki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4614, p.9-12. 在经济扩张过程中,信贷需求相对较高,这导致产生了更多的贷款,投资者一直愿意相对较高利率的贷款提供资金,这可能是因为投资者正在低利率环境中寻求更高的回报率,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市场贷款可能无法持续下去。
[25] See Peter Manbeck & Marc Franson,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place Lending: A Summary of the Principal Issues (2020 Update), American Banks Association White Paper, Sept. 2020, p.140-150.
[26] 对授信审查松懈、承销标准薄弱的激励也是美国对资产证券化模式的主要担忧。See supra note 4, David W. Perki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4614, p.1.
[27] 其实我国目前并无针对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硬性风险保留规则(Risk-Retention Rule),但是在实践中,例如花呗,通常会按照5%进行风险自留,参见蒋坤良:《蚂蚁花呗资产证券化案例分析》,西南科技大学2018年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企业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自留事实上是比照了央行和银保监会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要求,参见《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资产证券化发起机构风险自留行为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3〕21号)。另外,美国对于Marketplace Lenders是否适用Retention Rules存在的争议,主要是针对Marketplace Lenders仅将单比或几笔贷款出售做证券化的情形:通常认为该方式不需要遵循风险保留规则,因为Retention Rules适用于将许多贷款汇集成资产池再进行证券化的情况。对此,有观察者认为单笔贷款证券化下,放贷方依然存在着削弱承销标准的动机,需要遵循Retention Rules,而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单笔贷款的简单性(不同于众多贷款支持并具有复杂收益结构的证券)使投资者更容易理解自己所承担的风险,不需要遵守Retention Rules。See supra note 4, David W. Perki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4614, p.22. Also see Peter Manbeck and Marc Franson,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place Lending: A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 Issues (2016 Update), American Banks Association White Paper, April 2016, p.29-31.
[28] 有关监管规则除了对宏观风险防范具有一定意义,在居民杠杆率的控制方面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在报告中提到,需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1年2月8日,第45页,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9/5586209/files/0a68f9d82d6e480e953540a05b1367d8.pdf。由于本文侧重于对监管规则所表现出的审慎监管逻辑进行分析,因此在正文未对“控制居民杠杆率”的考量作出介绍。
[29] 参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整治办函〔2017〕141号,“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合并后的融资总额与资本净额的比例暂按当地现行比例规定执行,各地不得进一步放宽或变相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融入资金的比例规定。”
[30]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三)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31] 类似情况不止花呗一家,消费金融领域还有京东数科的白条(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和携程的拿去花(天津趣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等巨头也通过保理牌照实际从事放贷业务,并以保理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进行证券化融资。参见《花呗、白条、拿去花都在用这种牌照,地方刚刚出了监管办法》,载《第一消费金融》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Gn4uGljrmn1oNXxn6ez7g;《“拿去花”背后保理ABS不良大增 携程金融能否复制蚂蚁花呗小贷》,载《投资时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472126105329327&wfr=spider&for=pc。
[32] 例如在美国的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市场上,两房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作为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 GSEs)确立了贷款标准,要求贷方按照特定的程序和标准(比如Delegated Underwriting and Servicing process)对借款人进行评估,遵守标准化的承销和服务指南。See Darryl E. Getter,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Recent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6746, 2021, p.19.
[33] See Christopher K. Odinet, Securitizing Digital Debts,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Vol:52(2), p. 558-559 (2020). 国内亦有学者提出,算法本身的可信度难以审查,黑箱效应使得既有监管捉襟见肘。参见李敏:《金融科技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挑战及应对》,载《证券市场导报》2019年第2期。
[34] 参见张春丽:《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法律进路》,载《法学》2015年第2期。转引自吕璐:《机构改革背景下资产证券化监管法律制度研究——以市场流动性为中心》,载《金陵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
[35] Supra note 26, Peter Manbeck & Marc Franson, p.146.
[36]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本文主张对称监管,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信贷ABS的方方面面适用完全相同的监管规则。商业银行由于其特殊性需要接受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审慎监管,并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上进一步遵循风险资本计提的规则(参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与《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而非存款类放贷组织则无此必要。
[37] 参见前注34,吕璐文。
[38]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评级机构的结果并不全然可信(美国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的断崖效应值得警惕),但是在市场割裂的背景下,对于相同业务的同等监管上是需要加强的。
[39] See Allen & Overy, Alternative Credit Council, Non-bank Lend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19. Also see Alternative Credit Council, Financing European Business: Non-bank Lending and the Economic Recovery, 2020.
[40] Directive 2011/61/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8 June 2011 on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2003/41/EC and 2009/65/EC and Regulations (EC) No 1060/2009 and (EU) No 1095/2010Text with EEA relevance,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11:174:0001:0073:EN:PDF, accessed on March 17, 2021.
[41]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其他审慎监管指标比如,第十条规定的最低资本金: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
[42] 消费金融公司的杠杆率可达10倍,而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只有5倍,另外,消费金融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3亿元,远低于《征求意见稿》对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要求,参见《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另参见前注6,吴红毓然、胡越、张宇哲等文。
[43] 该问题之所以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我国对于非存款类放贷公司缺乏统一的监管规则,并且对不同放贷组织的差异化监管存在不合理之处。
[44] 参见华道世界:《蚂蚁集团:“借呗”“花呗”将全部纳入消费金融公司,申设个人征信公司》,载搜狐网,2021年4月13日,https://www.sohu.com/a/460503658_481514。
[45] 参见彭冰:《如何监管专业放贷组织——关于〈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载《法律与新金融》第4期。
[46] 参见盛学军:《互联网信贷监管新规的源起与逻辑》,载《政法论丛》2021年第2期。
[47] 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和美国都是挑战,甚至在联邦制的美国争议更大。目前,各州对于Marketplace Lending的市场准入施加了特定于州的条件,包括许可要求以及对产品和服务的限制,有评论者认为,消费者和市场参与者在冗余和自相矛盾的监管下受苦,而不是从保护市场的联邦制中受益。See Brian Knight, Federalism and Federalization on the Fintech Frontier,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 Technology Law, Vol. 20: 1, (Fall 2017), pp. 12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