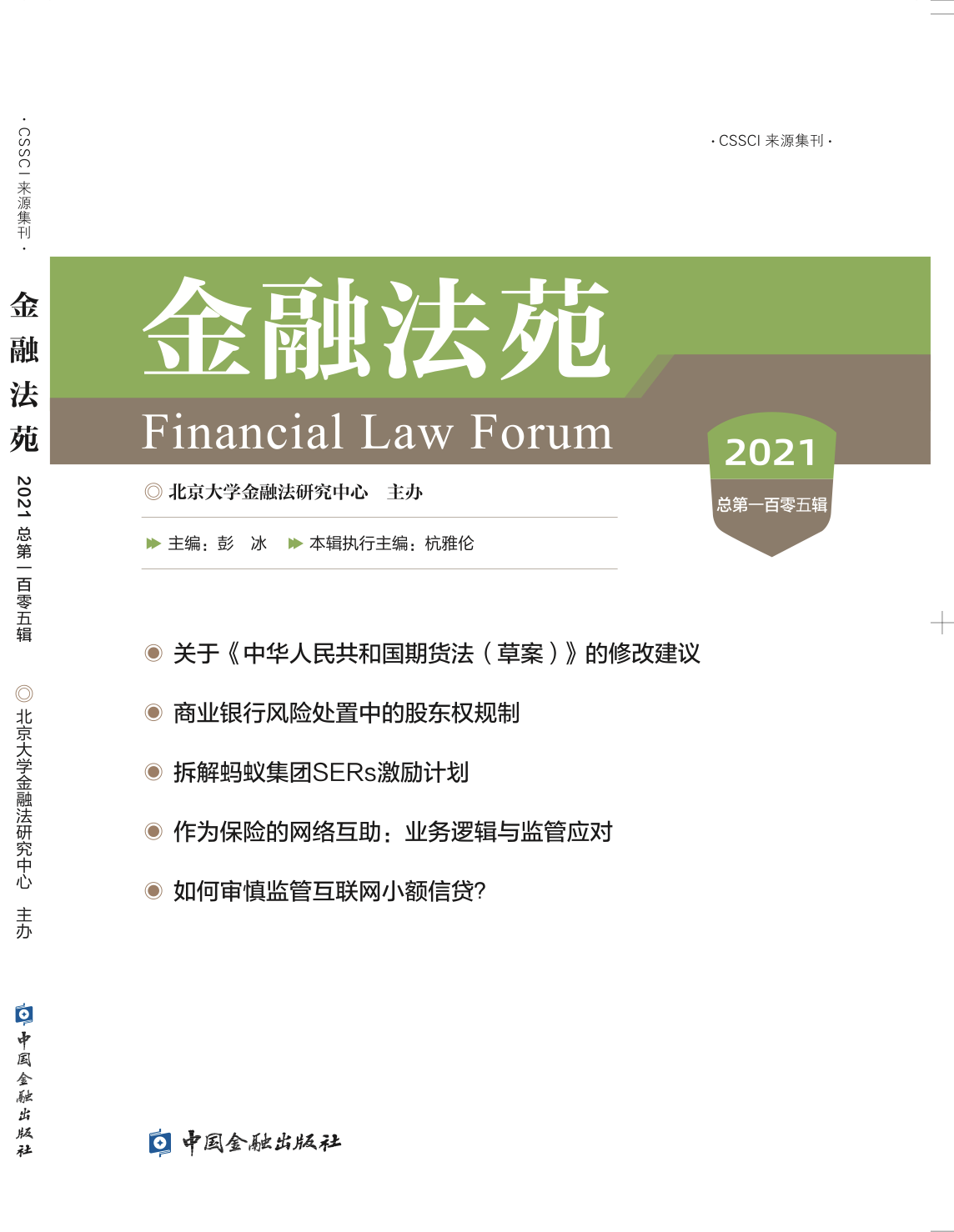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作者】邹星光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成文于巴黎布洛梅街3号,作者感谢楼建波老师、刘燕老师和彭冰老师对本文写作的指导,以及信托法读书会各位同学的宝贵意见。
【摘要】我国证券监管和部分理论研究都忽视了“发行人自身可能基于股份回购行为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这一问题,而该类内幕交易也会减损公众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投资信心。另外,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与内部人进行的内幕交易存在重大差别,因为前者实现的利益输送是从卖出股份的公众投资者流向未卖出股份的内部人和其他公众投资者。欧盟和美国都明确承认了发行人自身也可以成为内幕交易主体以及回购型内幕交易这一问题,但欧盟与美国的规制模式不尽相同。美国所采取的“同等对待”的规制模式实质上是对于问题的忽视,而欧盟对回购型内幕交易设置的特殊的安全港规则既能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又可凭借其明确具体这一优势消除回购行为的内幕交易嫌疑,从而促进回购这一资本运作工具的应用。从具体规制工具的角度来看,封闭期制度、回购计划执行情况的事后披露以及暂缓披露期间禁止回购是规制回购型内幕交易的刚性规则。
【关键词】股份回购 内幕交易 安全港
我国于2018年基于放松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回购(share repurchase/buy-back)的限制这一目的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目前正在考虑从公司资本制度等角度在新一轮的公司法修订中完善回购制度(如增加财源限制等)。总体来看,对于股份回购的规制体现为公司法和证券法两个层面:(1)公司法层面的回购规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和实现对股东的平等对待(fair treatment of shareholders);(2)证券法层面的回购规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或减少公众投资者受到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市场滥用行为(market abuse)的侵害。[1]本文无意对公司法层面的回购规则进行讨论,而是聚焦于证券法上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规制。
《公司法》“解禁”股份回购之后,证监会立即表示,“任何人不得利用股份回购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违法行为”[2];此外,学界也有少量文献专门讨论股份回购中的内幕交易这一问题[3]。但遗憾的是,监管者未能关注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部分学者的讨论也并未能真正厘清股份回购与内幕交易之间的关系。本文所称的“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是指股份回购行为本身构成内幕交易,这是股份回购与内幕交易之间最为特殊的关联,对于这类内幕交易也需要建立特别的规则。由于发行人能够回购自己的股份,因此其也可能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此即规制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逻辑起点,且这一逻辑前提在美国法和欧盟法上都有着十分清晰的体现。张巍教授在《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功能考察与制度反思———以美国经验为核心的研究》一文中关于美国法上对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设置的避风港(安全港)的介绍也很好地展现了发行人在股份回购中作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逻辑。[4]
下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就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法理逻辑与规制必要性进行了讨论。第二部分比较了欧美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规制模式,并提出我国应当借鉴欧盟的规则为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提供特殊的安全港规则。第三部分基于前文厘清的规制逻辑,针对具体的规制工具(安全港适用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一个简单的总结。本文的目的不仅是引起读者对公司自身也可能通过股份回购成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问题的重视,也期望能为对于证券法上的回购规则的功能性理解作出一些贡献。
一、逻辑前提:发行人作为内幕交易的主体
股份回购与内幕交易会在很多语境下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证监会会在以下两种情形将二者联系起来。其一是关注股份回购计划的披露。证监会强调,“在股份回购信息公开前,该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该信息的人,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进行处罚”,[5]即通过建立股份回购计划的事先披露制度来防止内部人(corporate insiders)实施内幕交易。其二是关注股东和管理层的“违法减持”问题。证监会强调,“上市公司相关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期间减持股份的,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6],其实质是股份回购的信号效应与事后的内幕交易的配合,即股份回购可以引起股价的上涨,而内部人可能基于未公开的内幕信息知悉这种上涨是高于股票的实际价值的,然后通过与事后减持相配合,就可以实现利益的输送。
但是,证监会关注的这两类情形都不是本文所讨论的 “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而是所谓的“内部人利用股份回购进行内幕交易”或者说是 “股份回购前后内部人的内幕交易”。所谓的“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是指股份回购行为本身是内幕交易,内幕交易的主体是公司自己,而非公司的内部人。具体操作模式是,当内部人认为股价被低估且未披露重大内幕信息时,其可以基于对公司的控制使公司在此时作出回购决议,从而通过在公开市场以低于股票真实价值的价格回购社会公众股东的股份来实现自身股份实际价值的上升,即所谓的低价回购(bargain repurchase)。相较于公司的某一内部人,公司这一整体更具有信息优势,其作为一个拟制的实体,最了解股价究竟是被低估了还是高估了。因此,我们会发现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与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在行为结构上是一致的,仅仅只是享有信息优势的主体不同而已。但是,根据我国《证券法》第五十一条(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第五十二条(对于知情人的定义)的规定,我国法上定义的内幕交易也只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内部人或知情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并且,2020年才被废止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证监稽查字〔2007〕1号)第十九条甚至直接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不构成内幕交易。[7]理论研究方面,许多国内经典的证券法学教材以及内幕交易研究专著在介绍内幕交易时都未考虑到在股份回购语境下公司自身作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情形。[8]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对于内部人利用股份回购进行内幕交易这一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比如,深交所和上交所在回购细则中针对内部人减持这一问题规定的特殊锁定期制度尤其值得商榷。[9]本文限于主题,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而聚焦于探析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这一在内幕交易规制理论上具有特殊性的现象及其规制逻辑。
虽然基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与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在行为结构上的一致,我们可以得出公司自身也可以从事内幕交易这一结论,但这仅仅是形式要件上的相符,要论证其规制必要性还必须从实质层面进行讨论。公司从事内幕交易这个说法很容易招致的反驳意见是,公司交易行为的受益群体是全体股东,所以并不需要规制,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获得直观的感受:
例如,A公司的股份共计100万股,内部人持股20%,外部股东持股80%。甲公司的股票价格为每股10元,但内部人基于信息优势知悉股票的真实价值为每股15元,公司的真实净值为15×100=1500(万元),此时甲公司以12元回购10万股;10万股外部股东持股被公司回购,剩余股东持有的股份为90万股,则此时公司的真实净值为1500-12×10=1380(万元),每股真实的净值为1380÷90≈153333(元),而此时每股实际价值的增值0.3333元也就是卖出股份的股东向未卖出股份股东的财富转移数额。并且,这与回购股份是否注销无关,因为公司自身对回购后的股份不享有权益;如果内部人在每股价值增值之后再出售自己持有的股票就可以将这一利益输送变现。
传统的内部人进行的违法内幕交易是实现利益从公众股东向知悉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的内部人的非法转移,违法的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本质上也仍然是内部人基于信息优势实现非法利益输送。由于公司本身只是一个拟制的实体,内部人只是通过公司作为主体从事的交易(回购)这一媒介来间接获益,这种非法利益输送就是其规制必要性之所在。但是,这种利益输送与内部人进行的内幕交易中的利益输送不尽相同,由于回购的仅仅只是部分公众投资者的股份,那么因回购而获益的股份不仅包括所有内部人持有的股份,还包括未被回购的外部股东持股,因此这种利益输送实际上是从卖出股份的股东(selling shareholders)流向未卖出股份的股东(non-selling shareholders),而并非所谓的使全体股东获益。[10]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基于信息优势产生的利益输送会破坏资本市场公平、损害投资者的信心[11],以及内幕交易需要被规制这一大前提,那么不论内部人是通过自己买卖股票来直接获益,还是通过公司回购股票来间接获益,都应当受到同样的法律规制。
并且,对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这种利益输送或者财富转移(wealth transfer)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规模不可小觑。Amedeo De Cesari等学者(2012)的研究指出,公司通过回购的获益(profits,包括股价的上涨与成本的降低两部分)与内部人的持股比例(insider ownership)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具体而言,以内部人持股比例为x轴,回购所获收益为y轴,则其呈现出一种“倒U形”的关系。因为随着内部人持股比例的增加,就会有更多“知情的投资者”(informed investors),从而使股票价格更为趋近其真实价值,所以当内部人持股比例超过一定数值,其带来的上述效应就会超过内部人信息优势带来的利益输送效应,从而使二者之间成负相关关系。[12]Richard Sloan和Haifeng You(2015)的研究表明,通过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的股份回购(bargain repurchases)和以高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的股份发行(inflated-price issuances)所实现的向长期股东的利益输送或财富转移(wealth transfer)平均占公司年净收益的40%,并且估计1973年至2008年这种财富转移总额高达2.8万亿美元。[13]
当然,这些实证数据给我们的启示仅仅只是内部人基于信息优势可以通过股份回购实现利益输送,但并不能说这种输送就是非法或者不当的,只有这种信息优势是基于未披露重大信息而获得的时候,我们才说其构成了证券法上的内幕交易。但是,这些实证数据至少对监管者应当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因为在如此大规模的利益输送中,很难说他们可能都是合法正当的。并且,这些合法或违法的基于信息优势在股价被低估时以低于股票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的回购最终会导致长期持股的股东(long-term shareholders)获得更多的收益,而这种财富转移会导致公众投资者整体上的预期利益减损,从而会增加公司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的难度。[14]
综上所述,公司自身作为主体的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与传统的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在行为结构上一致,且都有可能实现非法的利益输送,尽管输送对象有所差别,但却都会减损公众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投资信心。至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不论是内部人基于不法的信息优势买卖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还是公司基于不法的信息优势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回购自己的股份,二者都应当受到同等程度的规制。
二、欧美规制模式的分歧:特殊安全港与同等对待
那么,怎样才是上文所说的实现对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与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同等程度的规制”呢?其实质就是,对于发行人自身利用信息优势回购股票这一行为的规制应当比照对于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的规制来设计。由于美国法和欧盟法明确了发行人可以作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理念,本文这一部分通过介绍美国和欧盟的规则来理解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规制逻辑与模式。
美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模式。美国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与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确实是“同等对待”,对于前者并无特殊规则,二者适用相同的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但欧盟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并没有采取“同等对待”的模式,而是同时为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提供了“特殊的”安全港规则,即如若股份回购满足了特定条件,则可直接豁免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责任。美国法上也有股份回购安全港规则,即10b-18规则规则[15],但其仅仅只是操纵市场责任的豁免规则,并不涉及内幕交易。本部分主要分析欧美的规制路径分歧背后的逻辑,并对两种规制模式的效益加以比较,从而为我国提供有价值的制度参考。
(一)共同的规制起点:作为内幕交易主体的发行人
这一小节其实是对于本文第一部分内容的重申,主要是想证明,域外规则和文献清晰地树立了“公司/发行人也可能作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理念,这也是美国和欧盟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进行规制在法理上的逻辑起点。
首先,美国有大量的文献[16]和判例[17]指出,美国法上禁止内幕交易的10b-5规则[18]之规定同样适用于公司本身,其中规定的“任何人”(any person)也包括公司自身,SEC的立场也如此。[19]因此,公司本身也受到第10b-5条的限制,其在披露“重大”信息之前不得回购自己的股份。然后,就欧盟的规则而言,其于2003年颁布的《关于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市场滥用)的指令》[20](已废止)第8条与2014年颁布的《市场滥用规制法》(Market Abuse Regulation)[21]第5条所规定的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的安全港规则直接针对的也是发行人自身从事的股份回购行为,这证明欧盟立法者也清晰地认识到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这一问题以及发行人也应当是内幕交易规则的规制对象,即原则上发行人在未披露公司重大内幕信息的情形下不得回购自己的股份。
综上所述,尽管欧美的规制路径存在分歧,但对于发行人也可能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的清晰认识是二者的共性以及逻辑起点。
(二)欧美规制模式的比较:特殊安全港与同等对待
按照我们之前的逻辑,本来对于作为内幕交易的主体的发行人的规制应当等同于对于内部人的规制,但是欧盟法下特殊的安全港规则导致股份回购在满足了特定条件时可以直接、绝对豁免内幕交易责任。安全港规则意味着违反这些前提条件并不一定被认定为违法,而只是丧失了直接豁免的特权,然后需要根据内幕交易的一般构成要件对是否构成内幕交易进行实质判断。欧盟《市场滥用规制法》第5条对于执行股份回购计划豁免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规定的前提条件是:(1)在回购计划执行前对于回购计划的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2)依据回购计划所作的回购应当依法报告和披露;(3)符合对于回购价格和数额的限制;(4)明确回购计划的目的,且回购目的仅限于减资、用于转换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用于员工股票期权或股权激励这三种类型;(5)遵循欧盟在该法案后具体制定的相关技术性标准(technical standards)。欧盟2016年颁布的《关于市场滥用规制法的委员会授权补充规定》[22]进一步细化了《市场滥用规制法》第5条提出的标准,并规定了封闭期制度、回购计划执行期间不得卖出股份、不得在依法暂缓披露期间回购等限制性条件。
对于安全港这个问题,在此必须着重解释清楚的是,笔者并不是说美国法上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没有设置任何安全港,不过,此“安全港”非彼“安全港”。张巍教授在其文中已经介绍了,“公司可以利用预先设置好的,对于交易数量、日期、价格等因素无从事后变更的自动交易计划(所谓Rule 10b5-1交易计划)来实施股票回购,符合这种计划的回购不会被认定为内幕交易”[23]。但是,Rule 10b5-1交易计划(Rule 10b5-1 Trading Plans)并非针对股份回购设置的特殊安全港或豁免规则,而是同时适用于公司自身的交易(股份回购)与公司内部人的交易,故本文将美国模式定义为“同等对待”并无不妥。对于基于Rule 10b5-1 交易计划的交易进行豁免的逻辑是,这类交易是基于事先的计划而自动执行的,故无须考虑交易发生时公司或内部人是否存在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正因如此,适用Rule 10b5-1 交易计划这一安全港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公司必须证明回购计划颁布时并无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故这一安全港的适用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24]欧盟法上也有类似的逻辑,《关于市场滥用规制法的委员会授权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特别指出,如果回购行为是基于“回购时间预先确定的回购计划”(a time-scheduled buy-back programme)而作出,则回购行为无须满足第1款规定的在回购计划执行期间不得出售股份、不得在封闭期和延缓披露内幕信息期间进行回购等条件也可豁免市场滥用责任(即适用安全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6号)第四条也明确将“按照事先订立的书面合同、指令、计划从事相关证券、期货交易”的情形排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的范围之外。因此,法律上对于按照预定计划执行的交易的内幕交易责任豁免虽然也是一种安全港,且也可适用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但其与上文所介绍的欧盟法上针对股份回购型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提供的特殊的安全港的逻辑存在实质不同,后者的重要目的是减少市场滥用责任疑虑、促进回购。所以说,美国模式是一种同等对待模式,欧盟则是对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设置了“特殊的”安全港。
(三)安全港模式的合理性
介绍至此,需要直面的问题自然是何种模式更为合理。
欧盟对于这一问题的立法晚于美国,但其也并未解释过,为何在美国10b-18规则仅对股份回购型操纵市场提供了安全港的背景下,其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同时设置安全港。欧盟在《市场滥用规制法》的序言第(11)条中表示,公司基于经济上的原因在股份回购计划下交易自有的股份可能是合理的,所以应当让公司在特定情形下豁免关于禁止市场滥用的相关规定。然而,欧盟的这一解释并不充分,股份回购的经济功能并不能直接证成安全港这一规制模式,因为欧盟并没有说清楚同等对待模式的劣势所在。美国股份回购规则的历史能较为清楚地解释安全港的意义,尽管其针对的是操纵市场行为,但笔者认为其同样适用于对内幕交易的分析。经济学家Lenore Palladino教授指出,在美国建立10b-18规则之前,“尽管股份回购行为并非违法,但其容易招致(证券法上的)责任(open to liability)”;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SEC就开始考虑是否修改股份回购规则以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但直至里根政府时期才最终引入了股份回购的安全港规则;经济学家William Lazonick教授认为,自引入10b-18规则起,SEC开始了从股票市场的监管者(regulator)向促进者(promoter)的角色转变。[25]美国SEC前委员Jackson于2018年6月的发言也揭示了安全港模式的优势,其指出,安全港规则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美国SEC也接受了经济学界通行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股份回购行为往往是在公司具有信息优势的情形下作出的,而这将会导致股份回购行为很有可能触发证券法上的责任。[26]信号理论作为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股份回购动机的理论的同时,也恰恰加大了股份回购的内幕交易“嫌疑”。因为根据这一理论,由于内部人具有信息优势,当其知悉公司股价被低估时,可以利用股份回购向外部人释放股价被低估的信号,从而可以提升股价[27];一旦这种信息优势是基于未披露重大内幕信息而获得的,就会构成违法内幕交易。由此看来,股份回购的安全港规则,不论是针对操纵市场还是内幕交易,主要目的都是消除股份回购的违法嫌疑,从而打消市场主体的疑虑、促进回购。试想,如果根本就没有内幕交易的重大嫌疑,那为什么要建立特殊的豁免规则呢?作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我们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对其作无罪推定,而是对犯罪嫌疑人作无罪推定,原因正是他有重大嫌疑。当同时以“股份回购”与“内幕交易”作为关键词检索时,我们也会发现诸如“为何股份回购不被认为是内幕交易”(How are stock buybacks not considered insider trading)、“股份回购就是内幕交易吗”(Are corporate buybacks basically just insider trading)之类的疑问,这些公众提出的疑问也反映了股份回购所带来的直觉上的“内幕交易嫌疑”。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会让我们觉得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违法可能性更大。因为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往往是部分内部人买卖股票的行为,所以内部人之间存在“制衡”的机制。然而,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本质是内部人整体作出的“交易”(回购)决定,所有内部人或知情人作为一个整体受益,这其间并没有内部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衡,所以其违法可能性更高,即更有可能是在公司未披露重大信息的情形下进行交易。
综上所述,这种重大嫌疑可能会使上市公司因忌惮内幕交易(以及操纵市场)责任而不敢从事回购行为。尽管“重大(material)信息”这一模糊标准导致实践中察觉内幕交易行为的可能性很低,但这一模糊标准(standard)也是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会降低公司进行回购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将公司的行为规范规定为具体可循的规则(rules),只要回购行为遵循了这些客观具体的规则就可以豁免内幕交易责任,自然可以大为激励公司从事回购行为,这也符合鼓励回购的法律政策背景。因此,欧盟实行的安全港规则实质上是为了消除股份回购行为的内幕交易嫌疑,以鼓励市场主体通过回购实现合理的经济目的。虽然安全港规则中具体、刚性的规则无法完全消除内幕交易的可能,但至少还能较为确定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发生的可能(具体原因可参见下文对于具体规制工具的分析),还能节省“同等对待”模式下的实质审查成本。尽管安全港会“错放”一些实质上构成内幕交易的股份回购行为,而这种“错放”是实现鼓励回购这一目的、促进股份回购这一工具的经济价值的发挥所必要的社会成本。
至于为何美国法上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没有设置安全港,笔者猜测可能是美国法上的内幕交易监管规则的统一逻辑所导致,即美国法上对于内部人的内幕交易规制体系中欠缺与安全港规则中所需要的刚性制度相契合的思路。下文将具体介绍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一项重要的规制工具———尽管“重大(material)信息”这一模糊标准导致实践中察觉内幕交易行为的可能性很低,但这一模糊标准(standard)也是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会降低公司进行回购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将公司的行为规范规定为具体可循的规则(rules),[28]在该案中,SEC认为Andeavor在内控程序上未能保证其通过股份回购计划时无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而这是该公司董事会在作出股份回购授权时规定的要求。具体是指,未能通过合理的程序机制保证当时正处于磋商阶段的被收购计划不构成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因此,SEC认为Andeavor违反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3(b)(2)(B)节关于公司应当建立和维持足以合理保证公司从事的交易符合管理层的授权要求的内控体系的规定,从而课以2000万美元的罚金。虽然该案不是以内幕交易为由进行处罚,但也反映了SEC最近似乎开始重视股份回购中的内幕交易风险。[29]一方面,虽然美国法上一直承认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但并无相关处罚案例,这确实也导致安全港并不那么迫切需要。另一方面,Andeavor案这一新的监管动态似乎意味着公司从事股份回购行为需要开始重视内幕交易的嫌疑,而这种监管层面的关注一旦成为常态,安全港规则就实属必要了。
对我国而言,承认公司本身也可能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以及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乃法理逻辑之必然,也是解释现行相关规则(即下文介绍的具体规制工具)的依据。并且,我国股权集中的现状也要求监管者重视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这一问题。如若承认了这一问题,股份回购行为就会存在前述的“重大嫌疑”,从而也就需要安全港规则来消除嫌疑、促进回购实现其经济功能。因此,一方面,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在法理和实践层面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需要鼓励公司积极运用股份回购这一工具实现特定经济目的,故安全港规则对我国而言是合适的方案。另外,我国也存在建立安全港规则的制度条件,因为我国业已存在后文讨论的欧盟法上作为安全港的前提条件的封闭期、事后披露等具体规制工具。
三、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具体规制工具
上一部分讨论的是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规制模式,即美国法上同等对待传统的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和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模式以及欧盟法上为其提供特殊安全港的模式。本文这一部分讨论的不再是模式的问题,或者不再讨论立法上该如何对待公司基于股份回购作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问题,而是探讨那些实质上起到了规制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具体的、刚性的规则,即下文分析的“封闭期”“事后披露”“暂缓披露期间不得回购”等。在“同等对待”的规制模式下,这些具体的规则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与模糊的内幕交易构成标准(“重大信息”)相对应的规制工具,这些刚性规则可以弥补模糊的“重大信息”标准的不足。在“安全港”模式下,这些具体规制工具扮演的角色是安全港适用的前提条件。总之,不论采取何种模式,这类刚性的规制工具都是可以存在的。并且,尽管我国在监管思路和立法模式上并未考虑到公司基于股份回购成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可能性,但我国却在规则层面存在实质上起到规制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这一功能的工具。不过,由于对这些工具背后的逻辑和目的欠缺功能性的理解,现行规则尚需进一步完善,下文将进行具体阐述。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仅讨论对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规制,而不涉及操纵市场的问题。由于欧盟的安全港规则是统一适用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中找出针对内幕交易的规制手段。笔者认为,安全港规则中针对内幕交易的规制手段主要是封闭期、回购计划实施情况的事后披露以及暂缓披露期间不得回购等规则,下文具体对这三项制度的规制逻辑进行分析。
(一)封闭期
对于内部人从事内幕交易的规制而言,仅凭借“禁止基于未公开的重大内幕信息而买卖股票”这一规则,很难实现规制目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构成内幕交易要求未披露的信息达到“重大”的程度,而其判断标准本就是模糊的;另一方面,对于监管者来说,在每日成千上万的交易中发现违法内幕交易本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既然模糊的内幕交易判断标准的实效堪忧,那么我们可能不仅需要考虑这一弹性制度,而且需要考虑在刚性规则方面作出努力。这一刚性规则对于内部人而言就是在特定敏感信息披露前的“锁定期”(lock-up period)制度,对于公司回购自己的股份而言就是在特定敏感信息披露前的“封闭期”(closed period)或“封锁期”(blackout period)制度所谓的“封闭期”或“封锁期”就是指,在特定敏感信息披露前禁止或者限制公司进行回购。这种对应关系,就是前文提及的,对于内部人的规制手段对应于股份回购语境下安全港适用的前提条件。这种锁定期或封闭期其实就是推定在这一期间内部人或发行人自身已经知悉了某类价格敏感信息,所以禁止其在这一期间买卖股票,从而很大程度上减少内部人或公司利用这类信息从事内幕交易的可能。
欧盟于2014年颁布的《市场滥用规制法》第19条第11款统一规定,公司管理人员(person discharging managerial responsibilities)在依据交易所规则或依法应当披露的中期财务报告或年终报告公告前30个公历日内不得进行任何股票等金融工具的交易。[30]因此,基于统一的规制逻辑,对于公司回购行为设置的“封闭期”应当与针对管理人员的“锁定期”相对应。欧盟于2016年颁布的《关于市场滥用规制法的委员会授权补充规定》第4条规定,执行股份回购计划豁免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条件还包括,发行人在《市场滥用规制法》第19条第11款规定的期间内不得回购自己的股份,即统一建立了针对公司回购行为的“封闭期”制度。需要注意的是,欧盟建立的这一“封闭期”并不是一个禁止期间(prohibited period),在封闭期进行回购只是会导致这一回购行为无法直接豁免内幕交易,即如果该回购利用了未依法披露的重大信息则构成内幕交易。
然而,这种封闭期的制度并不是各国均存在的,采取这一制度的主要是欧盟国家。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封闭期的制度不是域外通行的制度,这是因为与之对应的“锁定期”也不是各国都有的制度,这是各国监管逻辑的内部统一性之必然结果。我们会发现,美国法上对于内部人的交易行为并没有这种在年报、中期报告等公告前的锁定期制度,自然其股份回购规则中也就没有对应的封闭期制度。但是,美国许多公司都会主动设置这种“封锁期”,例如“季度或年度财务报告公告前10日内”。[31]
就我国而言,《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号,以下简称《集中竞价回购补充规定》)第九条规定了“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这一封闭期。另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上交所回购细则》)第十八条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深交所回购细则》)第十七条也规定了“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这一封闭期(但是,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实施股份回购并减少注册资本的,则不受上述期间的限制)。这种封闭期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证监公司字〔2007〕56号)第十三条[32]是相对应的,这也体现了我国监管逻辑的内部统一。
但是,在上交所公布的《上交所回购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中,其对于封闭期的解释是,“《回购细则》保留了现行回购规则关于防范回购冲击二级市场正常交易的回购窗口期、申报价格等必要限制安排”,我们会发现其把前文提及的“封闭期”的功能定位为“防范回购冲击二级市场正常交易”,也即,其认为封闭期的功能是防范操纵股价,而忽视了前者所起到的防范内幕交易的功能。[33]这也印证了我国的监管者忽视了发行人作为内幕交易的主体这一问题。
(二)回购计划执行情况的事后披露
另一项具体规制工具与股份回购的信息披露相关。就回购计划的事前披露而言,其更多是针对内部人从事的内幕交易,即需要对作为重大的价格敏感信息股份回购计划本身进行披露,以防止内部人利用该重大内幕信息提前买入证券。但回购计划执行情况的事后披露却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规制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在事后披露制度中,需要核心讨论的问题是披露的时间点,下文将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时间点。
SEC在美国出现大量的“忽悠式”回购的背景下[34],于2003年建立了回购计划执行情况的事后披露制度,上市公司应当按季度向SEC报告其回购计划的实施情况。[35]欧盟2003年《欧盟委员会关于金融工具的回购计划与稳定措施的豁免规定》(已废止)[36]与2016年《关于市场滥用规制法的委员会授权补充规定》第2条第3款的规定是“回购交易实施后的第7个交易日前”这一披露和向监管机构报告的期间;英国[37]、澳大利亚[38]和我国香港地区[39]的规则是回购实施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披露;日本[40]等国采取的是按月披露的制度……我们会发现,这一披露期间的长度在域外很不统一,那这一长度的设置是任意的还是在设计时有独特的考虑呢?
就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规制而言,尽可能早地披露回购计划的实施情况可能有利于减少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给内部人带来的收益。如果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在进行回购交易的第二个交易日披露实施情况,投资者可能会趋向于认为公司回购的价格体现了公司的真实价值,从而调整其对于该公司股票的估值,这一调整至少会导致股价进一步趋向其真实价值;进一步的结果是,股价的上升会导致内部人在回购计划期间之后的交易中通过这种“低价回购”能获得的收益减少。但是,如果像美国一样采取按季度披露的制度,公众投资者无法透过公司披露的回购价格及时调整估值,市场就无法根据公司披露的回购交易的价格来迅速作出反应,公司就更有可能通过合法的或者违法的内幕交易来实现更大规模的财富转移。[41]当然,尚没有实证数据表明这种尽早披露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财富的合法或非法转移。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在《关于起草市场滥用规制法中技术性标准的最终报告》中指出,“回购交易实施后的第7个交易日前”这一披露期间的设置是合理的,因为其实现了在交易的透明度与披露成本之间的平衡。[42]但是,可以反问的是,既然我们未曾担心过管理层的股份变动在两个或三个交易日内披露这一制度(中国[43]、美国[44]等国均采取的是两个交易日内披露的制度;欧盟2014年《市场滥用规制法》第19条第3款统一采取的是交易后的三个交易日内披露和报告的制度)带来的成本,为什么又会觉得较为频繁的回购计划实施情况的事后披露会导致负荷过重呢?
如果更频繁的披露制度并不会造成过高的行政成本,那么我们的规则应当尽可能地提高回购交易的透明度和披露的及时性,让实际的回购价格尽早地为投资者所知悉,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人可能通过隐瞒内幕信息实现利益转移的规模。这在股份回购的纷繁规则中显得很不起眼,但正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期限设置在比较法上却形态各异,且这种多元化的规定并不是随意的,其背后有着独特的规制逻辑与考量。尽管究竟是选择两个工作日内披露还是周披露,这确实应当根据实践中的程序成本再作仔细的考量,毕竟在面对公众关于“是否应当继续坚持7个交易日这一披露期限或者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缩减”这一问题时,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很坚定地认为应当坚持这一披露期限,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期限设置是最有效率的[45],但是,至少立法者在设置这一期限时应当重视尽早披露对于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规制作用。
回观我国,我国的规则是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以披露、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46]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的规则应当尽可能地提高回购交易的透明度和披露的及时性,让实际的回购价格尽早地为投资者所知悉,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人可能通过隐瞒内幕信息实现利益转移的规模。因此,目前实行的“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的规则就很值得商榷,似乎与对董监高股份变动设置的“发生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内”这一期间保持一致更为合适。
(三)暂缓披露期间不得回购
此外,欧盟2016年颁布的《关于市场滥用规制法的委员会授权补充规定》第4条第1款3项还明确规定,公司在暂缓披露内幕信息的期间不得回购股份也是豁免市场滥用责任的条件之一。这一规定的逻辑是比较清晰的,既然有未披露的内幕信息,自然不适合再从事回购行为。我国法上虽然没有针对暂缓披露期间作出特殊规定,但《集中竞价回购补充规定》以及《深交所回购细则》和《上交所回购细则》都规定了“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这一窗口期,从而也能实际上起到禁止暂缓披露期间进行回购的效果。但是,从上交所的起草说明来看,这一窗口期的设置仍然是为了“防范回购冲击二级市场正常交易”,而似乎并无防范内幕交易的考虑。
四、结论
发行人可能基于股份回购行为而成为内幕交易主体,这是我国证券监管和部分学术研究所忽略的重要问题,而其是规制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逻辑起点。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会导致从卖出股票的公众股东到内部人和其他未卖出股票的公众股东的非法利益输送,欧盟和美国对此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模式。笔者认为美国所采取的“同等对待”模式实则是对于问题的忽视,而欧盟所采取的特殊安全港规则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内幕交易发生的可能,又可凭借其具体可感的优势消除股份回购行为的内幕交易嫌疑,从而促进股份回购这一资本运作工具的应用。对于我国而言,安全港规则的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有必要,现行法中的具体、刚性的规制手段也是我国建立安全港的优良条件。另外,我国也应当基于规制内幕交易的目的,进一步完善事后披露制度等具体规制工具。
对于本文最大的质疑可能是,既然我国已经有了客观上起到规制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的规制工具(封闭期、事后披露等),那么对规制工具加以完善岂不足矣?又何须多此一举通过安全港规则来豁免责任?这一质疑是短视的,我国现行的模式之所以看上去平安无事,恰是因为监管者并未意识到股份回购型内幕交易所带来的非法利益输送这一问题。对于这一质疑的有力反驳是,明确了发行人作为内幕交易主体这一前提,如果监管者日后发现遵守了具体规制工具的要求,而实质上仍然属于内幕交易的股份回购(即存在不当利益输送),是否要处罚呢?一旦处罚了,这种处罚所带来的股份回购的内幕交易嫌疑和市场主体的疑虑又该如何处理?既然如此,为何不未雨绸缪,完善规则供给?所以,最终还是得靠安全港规则来解决这一矛盾,即为满足具体、刚性条件的回购提供内幕交易责任的安全港。
[1] 关于股份回购规则的体系,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Report on “Stock Repurchase Programs”, 2004.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37号。
[3] 参见李晓春:《股份回购中内幕交易行为之证券法规制》,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12期;谭婧、徐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中的失信行为及其防范》,载《证券法苑》2012年第2期。
[4] 参见张巍:《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功能考察与制度反思———以美国经验为核心的研究》,载《证券法苑》2017年第4期,第89页。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37号。
[6]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37号。
[7] 类似地,2020年废止的《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证监稽查字〔2007〕1号)第四十八条也规定,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不构成操纵行为。
[8] 参见彭冰:《中国证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朱锦清:《证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贺绍奇:《“内幕交易”的法律透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杨亮:《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胡光志:《内幕交易及其法律控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井涛:《内幕交易规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9] 以上交所发布的回购细则为例,其第二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而回购股份,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得在公司回购股份期间直接或间接减持本公司股份,即一种特殊的锁定期制度。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28条更是不论回购目的都设置了该锁定期,但在美国和欧盟的规则以及欧盟主要成员国历史上的规则中并未检索到类似做法。国外有学者(See Jesse M. Fried, Insider Signaling and Insider Trading with Repurchase Tender Offers, 67(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21 (2000), pp. 421-477)主要基于大量表明“内部人趋向于在股份回购计划宣布后减持”的实证研究(See, e.g., Henock Louis, Amy X. Sun, and Hal White, Insider Trading After Repurchase Tender Offers: Timing Versus Informed Trading, 39 Financial Management 301(2010), pp.301-322)而提出应当在股份回购的语境下建立相应的锁定期制度来规范上述违法减持问题,但我们也会发现大量诸如“内部人趋向于在盈利公告之后减持”“内部人趋向于在增发公告之后减持”等研究结论。那法律是不是在这些利好消息的公告后都需要设置一个锁定期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早就有研究(See, e.g., Seyhun, H. Nejat, Insiders Profits, Costs of Trading, and Market Efficiency, 16(2)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89(1986), pp. 189-212)指出内幕交易具有所谓的“逆向本质”(the contrarian nature of insider trading),即内部人趋向于在利好消息公告后卖出,在利空消息公告后买入。因此,关于某类特定的利好消息后的内部人减持现象的研究可能是大量存在的,这些实证数据本身并不能证成某类特定消息公布后减持行为的特殊规制需求。原因很简单,这种利好消息太多了,如果都设置一个刚性的锁定期,就会过度限制内部人的转让权,从而会过分降低内部人持股的积极性。因此,仅基于实证数据尚且很难论证设置这一特殊锁定期的必要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SEC前委员Jackson提出,将这种锁定期作为股份回购型操纵市场责任的安全港的前提条件,不失为一种妥当的方案,具体参见Robert J. Jackson Jr., Stock Buybacks and Corporate Cash-outs, 2018, https://www.sec.gov/news/speech/speech-jackson-061118#_ftnref9, accessed on December 3rd 2018.
[10] See Jesse M. Fried, Informed Trading and False Signaling with Open Market Repurchases, 93 Calif. L. Rev, 1323 (2005), pp.1323-1386.
[11] See, e.g., Brudney V., Insiders, Outsiders, and Informational Advantages under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93 Harv. L. Rev. 322(1979), pp. 322-376; Karjala D S., Statutory Regulation of Insider Trading in Impersonal Markets, Duke LJ 627(1982), pp.627-649.
[12] See De Cesari, Amedeo, et al., The Effects of Ownership and Stock Liquidity on the Timing of Repurchase Transactions, 18(5)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023(2012), pp. 1023-1050.
[13] See Sloan, Richard G., and Haifeng You, Wealth Transfers via Equity Transactions, 118(1)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93(2015), pp. 93-112.
[14] See Jesse M. Fried, Insider Trading via the Corporation, 16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801(2013), p.828.
[15] 17 CFR 240.10b-18-Purchases of certain equity securities by the issuer and others.
[16] See Mark J. Loewenstein, and William KS Wang, The Corporation as Insider Trader, 30 Del. J. Corp. L 45(2005), pp.58-59.
[17] See Mark J. Loewenstein, and William KS Wang, The Corporation as Insider Trader, 30 Del. J. Corp. L 45(2005), pp.61-70.
[18] 17 CFR 240.10b-5-Employment of manipulative and deceptive devices.
[19] See Mark J. Loewenstein, and William KS Wang, The Corporation as Insider Trader, 30 Del. J. Corp. L 45(2005), p70.
[20]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3 on insider dealing and market manipulation (market abuse).
[21] Regulation (EU) No.596/201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6 April 2014 on market abuse (market abuse regulation)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Commission Directives 2003/124/EC, 2003/125/EC and 2004/72/EC(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2]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16/1052 of 8 March 2016 sup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No.596/201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with regard to regulatory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the conditions applicable to buy-back programmes and stabilisation measures(Text with EEA relevance).
[23] 参见张巍:《上市公司股票回购的功能考察与制度反思———以美国经验为核心的研究》,载《证券法苑》2017年第4期第89页。
[24] 17 CFR § 240.10b5-1(c).
[25] See Emily Stewart, Stock Buybacks,Explained,资料来源:https://www.vox.com/2018/8/2/17639762/stock-buybacks-tax-cuts-trump-republicans, 2018年12月3日访问。
[26] See Robert J. Jackson Jr., Stock Buybacks and Corporate Cash-outs, 2018,资料来源:https://www.sec.gov/news/speech/speech-jackson-061118#_ftnref9,2018年12月3日访问。
[27] See, e.g., Theo Vermaelen, Common Stock Repurchases and Market Signaling: An Empirical Study, 9(2)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9(1981), pp. 139-183.
[28] See SEC, Release No. 34-90208, Oct. 15, 2020.
[29] See Ignacio E. Salceda, Douglas K. Schnell, Recent SEC Action Brings Fresh Focus to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in the Share Repurchase Context, October 21, 2020,资料来源:https://www.wsgr.com/en/insights/recent-sec-action-brings-fresh-focus-to-material-non-public-information-in-the-share-repurchase-context.html,2020年12月27日访问.
[30] 当然,这种锁定期在欧盟制定统一规则之前就出现在了欧盟国家的立法例之中,例如英国《上市规则》第9章附件1“标准守则”(Model Code) 就规定了年度报告或季度报告公告前60个工作日的锁定期。
[31] Se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Report on “Stock Repurchase Programs”, 2004, p.12.
[32]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证监公司字〔2007〕56号)第十三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一)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二)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三)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四)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33]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封闭期也有规制操纵市场的功能,认为股份回购可能构成操纵市场的逻辑在于公司通过回购释放股价被低估的这一信号是错误性或者误导性的(falsesignaling),因此在封闭期内禁止回购的意义也包括防止内部人在已经知悉公司真实价值的情形下释放错误信号。参见朱庆:《股份回购操纵市场“灰色地带”的形态及其法律规制》,载《法学》2011年第9期,第89页。
[34] See Jesse M. Fried, Informed Trading and False Signaling with Open Market Repurchases, 93 Calif. L. Rev, 1323 (2005), pp.1351-1352.
[35] 17 CFR 240.10b-18-Purchases of certain equity securities by the issuer and others.
[36]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2273/2003 of 22 December 2003 implementing Directive 2003/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exemptions for buy-back programmes and stabiliz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37] FCA Handbook: Listing Rules 12.4.6.
[38] ASX Listing Rules 3E Daily share buy-back notice.
[39] HKEX Main Board Listing Rules 10.06 (4).
[40]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Exchange Act Article 24-6 (1).
[41] See Jesse M. Fried, Insider Trading via the Corporation, 16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801(2013), pp.835-837.
[42] See Final Report: Draft technical standards on the Market Abuse Regulation, 3.2.2.3 Deadline for public disclosure, ESMA/2015/1455, p.14.
[43] 参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证监公司字〔2007〕56号)第十一条。
[44]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 16(a), 15 U.S.C. § 78p (a).
[45] See Discussion Paper: ESMA's policy orientations on possible implementing measures under the Market Abuse Regulation, 14 November 2013, ESMA/2013/1649, p.10.
[46] 参见《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号)第六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四十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