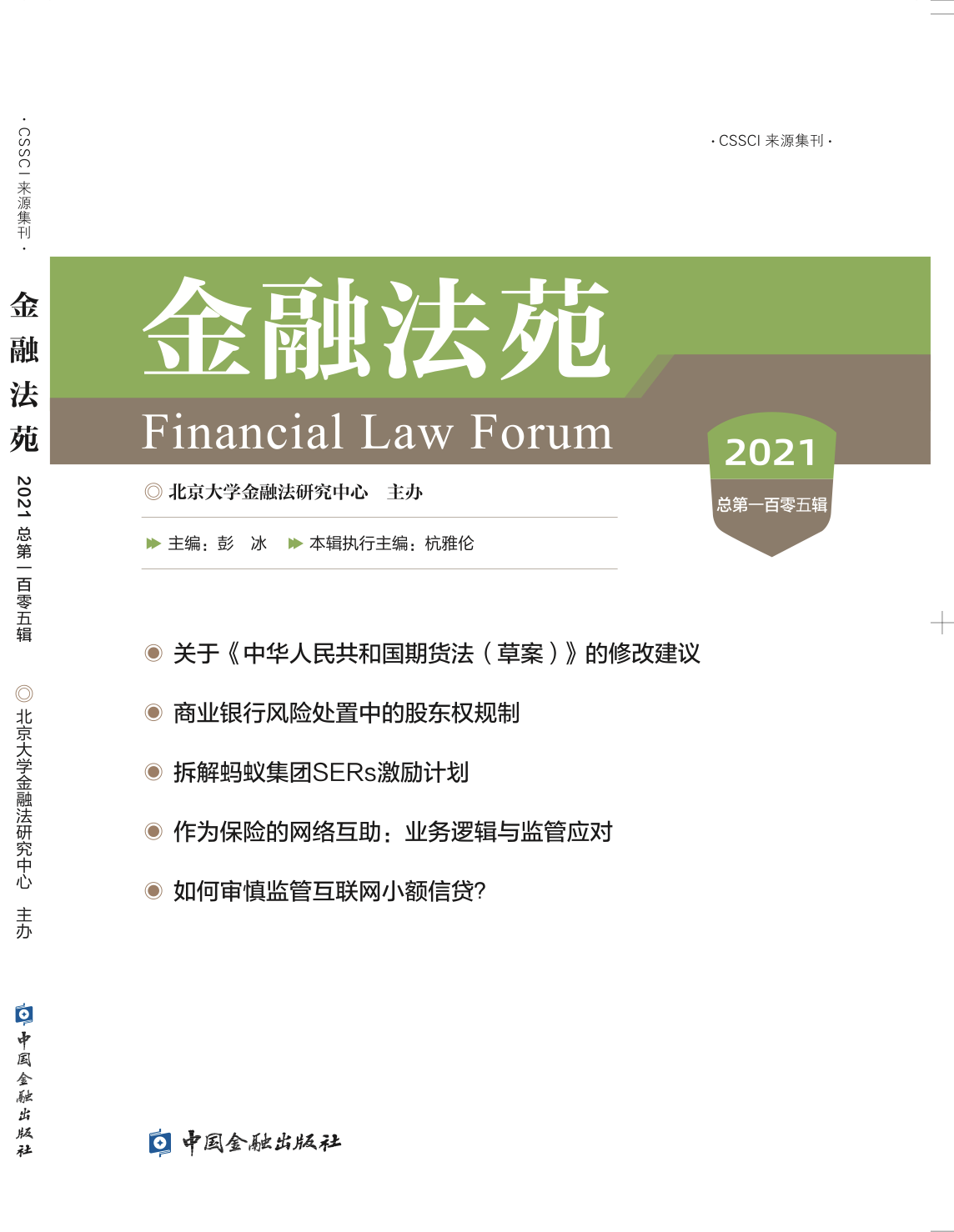作者:李云飞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兼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金融刑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金融稳定处。
摘要:《美国法典》第5324节规定的拆分现金交易罪是美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维护了大额交易报告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中美在犯罪观念上存在本质的区别,美国的立法未必能完全适应中国本土的刑事法律观念,但其要求金融机构的客户承担反洗钱配合义务,并匹配相应责任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启迪。我国反洗钱立法体系中单项性地规定了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缺少对客户反洗钱配合义务和相应责任的规定。这种责任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反洗钱制度整体功效的发挥。在责任体系的完善上,刑事法律不能贸然挺进,但行政法律责任则应予完善。
关键词:大额现金交易报告;洗钱;拆分交易;刑事立法
“1986年,美国国会在创制1956节并将其作为打击洗钱犯罪的一般性规定的同时,在5324节创制了一项特别的反拆分交易罪。”[1]美国反洗钱刑事立法是一个体系性概念,在这一体系中,除了以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助推犯罪行为等为核心内容的《美国法典》第1956、1957节的规定外,《美国法典》第5324节规定的拆分现金交易罪[2]也是美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国内学者认为的拆分现金交易的行为在美国不是一项独立的罪名的见解,[3]本文不敢苟同,并希望能通过本文让读者全面了解该罪的“前世今生”。
一、拆分现金交易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演变
(一)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的出现
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的建立是“与洗钱作斗争的第一场战役”。[4]“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毒品问题迅速恶化,毒品滥用问题不再局限于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开始超越阶层、族裔、性别、年龄的界限向美国主流社会扩散,不仅对公众健康构成重大威胁,而且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遂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5]毒品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相滋相伴”成为美国社会的症结,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早期采取的是“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取得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957—1967年的10年间,尽管三届美国总统、三任司法部长以及数以百计的联邦特工和检察官为追诉和审判黑手党成员做了种种努力,采取了各种措施惩治有组织犯罪,但屡遭挫折、成效甚微”。[6]执法部门发现很难将有组织犯罪的高层人员与马仔所实施的具体犯罪联系起来。最终只能以偷税等罪名对有组织犯罪的领导者提起诉讼,即使能将有组织犯罪的头目绳之以法,很快就会有其他人代替原有领导者继续领导该组织从事犯罪行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打击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策略发生变化,打击的重点从单纯地打击毒品犯罪和有组织犯罪行为本身转向打击上游犯罪与剥夺犯罪资金并行的轨道上。[7]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970年通过了《银行保密法》,[8]其规定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成为打击洗钱行为的最初手段。美国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包括以下四类:
一是现金交易报告(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CTR),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报告形式。根据《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篇第5313节和第5325节的规定,金融机构等报告主体必须就同一交易日内,由同一客户或由同一客户控制实施的单笔或累计多笔总额大于1万美元的存款、取款、兑付等现金交易,按照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的“104表格”(赌场按照103表格)提交现金交易报告。[9]
二是根据《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篇第5331节的规定,任何从事贸易或提供商品服务的主体在为客户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一次或多次接受与该笔交易相关的现金累计超过1万美元的,应根据《1986年国内税收法》第6050I(g)的规定提交符合“8300报表”规定的大额交易报告。[10]
三是根据《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篇第5316节的规定,任何人在出入美国国境时,对携带超过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均需提交“105格式”的大额现金报告,这种报告称为CMIR。“CMIR 与《银行保密法》规定的其他类型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最大不同点在于 CMIR 报告的提交主体不是银行也不是特定非金融机构而是携带现金出入境的主体自身。”[11]
四是《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篇第5314节规定的海外银行账户报告(the foreign bank account report, FBAR)。要求对持有海外银行账户且资金超过1万美元的个人,每年须申报一次该报告。
在上述四种交易报告中,前三种均存在拆分现金交易规避大额交易报告的可能。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均属于第5324节规制的对象,拆分现金交易规避 CMIR 的行为根据第5332节规定的大额现金走私罪定罪处罚。
(二)拆分现金交易行为刑事立法化进程
在《银行保密法》通过的早期,该法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12]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未按规定提交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受到严厉的惩罚之后,《银行保密法》的规定才真正落到实处。[13]犯罪组织为了绕过这种洗钱障碍,“开始进行精心的策划,把从犯罪活动中攫取的收益化整为零地分散成很多笔数低于临界最低限额的款项”,[14]一种新的犯罪手段开始出现——拆分交易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最早一起拆分现金交易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案件是1979年发生的 United States vs Thompson 案,自此以后,以拆分交易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案件开始不断地涌现。[15]
“1986年以前,法律对拆分交易的行为并未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16]早期对拆分交易行为的定罪理由不一,有将拆分交易的行为人拟制为金融机构的,将其拆分交易的行为视为违反金融机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义务:[17]也有将其作为欺诈行为进行处理的:[18]但最为流行的理由还在于将拆分交易行为视为拆分交易者通过拆分交易帮助、教唆金融机构不提交大额现金交易报告。[19]但上述对拆分交易进行归责的理论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毕竟个人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履行报告义务的金融机构,将个人拟制为金融机构于法不符。[20]依据教唆犯理论对拆分交易的主体进行归责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21]
为解决行为人通过拆分交易规避大额交易报告定罪无明确法律依据的问题,1986年通过的《洗钱控制法》将其规定为犯罪行为,编入《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编第5324节。[22]并成为“里根政府反毒品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3]“从此,拆分现金交易或企图拆分现金交易以使大额交易报告义务主体无法提交交易报告或无法正确提交交易报告的行为将依据第5324节的规定进行定罪。”[24]第5324节由(a)(b)(c)(d)四项构成,(a)(b)(c)项分别针对《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编第5313(a)节和第5325、5331、5316节中规定的大额交易报告要求作出刑事禁止性规定,禁止行为人以规避大额交易报告为目的,实施或试图实施能造成提交报告的主体无法提交报告或无法正确提交报告的行为或拆分交易的行为,(d)项是罚则规定。1986年通过《洗钱控制法》之初,对违反第5324节之规定的行为并未单独设立刑罚,在1994年9月以前对违反第5324节规定的行为均是依据筹备组5322(a)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1994年国会在修订第5324节时将其刑罚规定从5322(a)中独立出来,作为5324(d)项单独规定。[25]
二、拆分交易行为热点问题研究
(一)违法性认识有无的争议及主观要素认定的实践模式
1.违法性认识有无的历史争议。
本罪主观方面需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拆分现金交易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在美国争议很大。1994年以前的争议主要围绕“willfully”一词在刑事法律中的含义而展开。[26]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主观上不需要有违法性认识。法院应根据“不知法律不免责”的法律原则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willfully”一词在刑事法律中的含义通常仅包括行为人对行为的认识而不包括行为人对行为本身违法性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虽需违法性认识,但违法性认识无须证明。“一般情况下行为人的拆分行为主观上都包含罪过因素,无罪过不是该种行为主观上的典型特征,因此,可以据此合理认为行为人故意拆分交易避免大额交易报告的行为在主观上具有恶性,违法性认识无须证明。”[27]
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缺少违法性认识或法律认识错误不能成为辩护理由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根深蒂固,但就本罪而言违法性认识是构成本罪的必备要素。拆分交易行为的主观目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虽然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会采取拆分现金的方式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掩饰犯罪行为。但并不能以此推断行为人的拆分行为主观上都具有恶性。如行为人害怕因报告大额现金交易暴露自己的财产情况,引起盗窃等案件因而在存取现金时采取拆分的方式,主观上很难认定行为人存在主观恶性。再比如通过拆分现金合理避税的行为,都很难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恶性。[28]因此不能认为拆分现金的行为本身具有内在的恶性,行为人的故意行为本身并不内含违法性认识。对行为归责的依据不在于拆分交易的本身,而在于行为人知道拆分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却铤而走险的主观恶性。
上述几种观点均得到了判例的支持。如美国联邦第一巡回法院1987年在审理 United States vs Bank Of New England 一案中认为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有违法性认识。[29]而1994年发生的 Ratzlaf vs United States 一案,则成为该罪在主观上是否要有违法性认识的分水岭。戏剧性的是针对该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美国国会在行为人主观上是否要有违法性认识的问题上给出了完全不同、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由于该案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成为美国学者引用率非常高的一个案件,现简要介绍如下:
1988年10月20日晚,被告人 Ratzlaf 在美国雷诺市的一家赌场欠下16万美元债务,在债务到期日, Ratzlaf 怀揣10万美元现金来到了该家赌场。赌场经理告诉 Ratzlaf,超过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赌场需向州和联邦的监管机构报告,但如果使用银行本票则无须报告。 Ratzlaf 决定将现金存入银行购买银行本票, Ratzlaf 来到银行后,银行员工同样告诉 Ratzlaf,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银行需要提交大额交易报告。为规避大额交易报告, Ratzlaf 将10万美元现金分别存到了不同的银行,且每家银行所存金额均小于1万美元。 Ratzlaf 采用这种拆分交易的方式在不同的银行一共购买了10万美元的银行本票。基于上述事实,检方以 Ratzlaf 违反了《美国法典》第5322(a)节和第5324节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得到法院支持。 Ratzlaf 向第九巡回法院提起上诉, Ratzlaf 认为自己虽然认识到银行有报告大额交易的义务,本身也有拆分交易规避报告的目的,但根本不知道拆分交易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其主观上不符合第5322节中“故意违反规定”(willfully violating)的主观要求。第九巡回法院驳回了 Ratzlaf 的上诉。一审法院和第九巡回法院均认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拆分交易的目的即为已足,至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是“故意违反法律”不能成为抗辩之理由。[30]
与第九巡回法院的观点不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本案中在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时,应能证明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违法性认识。此后不久,对最高院的解释,国会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国会对第5324节进行了修改,在条文表述上不再使用“willfully”一词,[31]只强调行为人主观目的,只要是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故意规避大额交易报告的目的即为已足,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违法性认识。[32]
2.对犯罪心理认定的实践模式。
虽然自从 Ratzlaf 案之后,违法性认识不再被认为是构成本罪的必备要件。但检方仍必须证明行为人在主观上知道金融机构有报告大额现金交易的义务,[33]并且主观上是出于规避大额交易报告的目的。在认定行为人犯罪心理方面,主要有两类证据:一类是直接证据:一类是间接证据。前者如行为人自己的供述,后者如根据被告的行为间接推断行为人犯罪心理的相关证据。“令人惊奇的是,在许多案件中,行为人对拆分交易以规避大额交易报告的目的供认不讳。行为人规避大额交易报告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怕麻烦,如银行填写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会耽误客户时间。二是银行柜台人员告诉客户如此行事。”[34]
在间接证据的使用上,主要是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来推断行为人的犯罪心理。陪审团可以从被告拆分交易的行为惯性或行为模式上以及行为人以前进行过的大额交易的事实上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知道银行有报送大额交易报告的义务并且行为人有规避大额交易报告的目的。[35]通过行为模式来认定犯罪心理存在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这种行为模式必须十分明显,行为的共性特征必须十分突出,即便如此,在据此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仍有可能存在证据不充分的问题。二是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频繁存取小额现金的需求,对这种行为就不能依据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来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如对一些小零售店来说,为了防止留存过多现金被抢,行为人可能经常会将一些1万美元以下的现金存入银行,此外还有一些现金需求比较大的零售企业,也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而出现经常存取现金的行为,对这些行为就不能单单依靠行为人的行为模式来认定其主观状况。[36]
因此在确定行为人主观状况时,除了要考虑行为模式外还要结合其他因素来具体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况。如调取行为人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交易情况:分析行为人的交易是否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行为人是否存在利用多家银行进行小额交易:行为人牺牲交易的便利性和效率性的行为是否合理等。
此外,一些特定人员的职业背景也可以作为认定其主观状况的证据。如处于一线工作的银行雇员由于其有提交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义务,因此可以推定其在拆分交易时的主观状况。此外,还可以根据行为人是否接受过相关的反洗钱培训来推定行为人主观状况。
(二)对“拆分”行为的辨析
1.拆分行为定义。
第5324节未对“拆分”行为进行定义。但美国财政部对“拆分”行为进行了解释,其外延较广泛。所谓“拆分”是指“行为人自己或与他人一起或代表他人通过一家或多家金融机构在一天或多天内实施或试图实施的以规避《美国行政法汇编》第31篇第103.11节(31 C. F. R.§103.11,即关于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相关要求,作者加)为目的的单笔或多笔现金交易行为,交易金额在所不问。行为人拆分交易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行为人将一笔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拆分成多笔1美万元(包括1万美元)以下的现金进行交易。”[37]
2.拆分的对象是“现金”。
报告主体不同“现金”含义也不同。对银行和赌场来说,“现金”是指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正在流通的法定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以及在美国还可以流通的银币券、国家券和联邦储备券,还包括在国外习惯上作为交换媒介并广为接受的银行票据。个人支票、银行本票和银行汇票等可转让票据不属于“现金”的范围。
对按规定应当提交8300格式报告的主体来说,“现金”的概念更为宽泛。银行本票、银行汇票、现金支票[38]、旅行支票等可转让票据也属于“现金”的范围。[39]
3.资金性质对拆分交易犯罪的影响。
第5324节对行为人出于何种动机,拆分的资金来源合法还是非法,都在所不问。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行为人采取了法律所禁止的方法规避大额交易报告。
但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对拆分交易的定罪量刑在两方面产生影响。一是如果所拆分之资金经证明确来自于犯罪所得,即可推定行为人拆分交易之目的是为了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二是如果行为人拆分交易之资金来源于特定的犯罪所得,会出现法条竞合的问题,即该行为在符合第5324节规定的同时也符合《美国法典》第十八编第1956(a)(1)(B)(ii)[40]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由[41]1956(a)(1)(B)(ii)的刑罚要比第5324节规定的严重,在实践中一般按第1956节的规定定罪量刑。
4.对拆分交易行为罪数的认定。
对拆分交易行为罪数的认定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在所拆分之交易的资金来源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罪数更为困难。在认定罪数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一是以资金来源的个数作为认定标准。如果行为人对一笔资金分多次进行拆分,认定为一个犯罪。“引起犯罪个数计算问题最早的一个案例是 United States V Davenport 案。”于在该案中法院提出了应以资金的来源数作为认定罪数依据的理论。该案发生在1991年,被告在2周内分10次将总计81500美元的现金存入银行,每笔交易均小于1万美元。检方据此指控被告犯有10个拆分交易的犯罪行为。法院认为拆分行为而不是存款行为,是认定犯罪个数的标准。拆分交易犯罪的本质就是通过拆分交易行为,将金额较大的交易拆分成金额较小的交易,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因此不能以具体的存或取款的行为个数来认定拆分交易的罪数。法院认为这10笔交易实际上构成了1个拆分交易的犯罪行为,因此对行为人定一罪。[42]
同年发生的 United States V Nall 案中第10巡回法院也认为不能以行为人实施的拆分交易中的具体存款行为的次数认定犯罪个数,应以所拆分之资金来源是否单一为标准。[43]除此以外还要考虑行为人的行为目的,如果所拆分之资金虽有多个来源,但均服务于行为人的一个统一的交易目的,仍算作一个犯罪行为。
依据资金的来源个数认定拆分交易行为个数的方法也有其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分次取款的行为中,便无法根据资金的来源个数认定犯罪个数。
二是以时间跨度作为认定犯罪个数的标准。在不能识别出行为人所拆分之资金来源是否同一的情况下,提出了另外一种以行为的时间跨度作为标准的理论。如以12个月作为标准,凡是在12个月内所实施的拆分行为均计算为一个犯罪行为。但这一理论在司法实践中遭到了抵制,如在 United States v Handakas 一案中,[44]法院就拒绝使用这一理论计算罪数问题。法院认为这种计算罪数的方式缺乏法律依据。
三是以行为的时间间隔作为认定犯罪个数的标准。在 United States v Catherman 一案中,[45]检方提出了一个关于计算拆分交易行为的新方法,即以上一次拆分交易与下一次拆分交易的时间间隔来计算拆分交易的行为个数,如果两次拆分交易的行为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则确定为两个不同的拆分交易的行为。
三、对拆分交易行为的量刑
5324(d)对拆分交易的行为规定了两个档次的量刑标准。一是拆分交易行为的通常处罚标准,即对行为人处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两者并处。二是情节严重的处罚标准。即如果行为人在实施了拆分交易的同时又违反了美国其他法律,或者在连续的12个月内拆分交易的涉案金额超过10万美元以上的,对行为人处5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并罚。《量刑指南》2S1.3节对如何具体量刑做了规定。
拆分交易犯罪的基本刑量是6级,在此基础上随着拆分交易金额的增加其刑量也不断增加。具体计算以《量刑指南》§2B1.1规定的《刑量对应表》为准(见表1)。

除了金额以外,以下几个因素也影响本罪的刑量:
一是资金是否来自于违法犯罪所得或拆分交易的目的是否为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根据2S1.3(b)(1)的规定,“如果行为人知道或相信所拆分的资金来自于非法所得或用于从事非法活动,或者所拆分的资金来自于大额的现金走私,则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档次。”实际上如果行为人所拆分的资金来自于非法所得或用于从事非法目的的,应按照1956节有关洗钱罪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罚。
二是如果行为人在12个月内两次以上实施拆分交易行为且总金额超过10万美元以上的在量刑上提升两个档次。[47]
三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中不存在以上两点因素,且所拆分之资金来源合法,用途合法,行为人主观上对资金来源是否合法也不是持有轻率心态的,对其刑量应调整为6档。[48]
《量刑指南》以行为人拆分交易所涉金额作为确定量刑标准的依据。在涉案金额较小的案件中,《量刑指南》规定的量刑标准相对较低,量刑档次与盗窃、欺诈和洗钱犯罪的基本量刑档次一致。“这与量刑委员会对行政犯一向的态度是一致的。”[49]但随着拆分交易金额的逐步增大,基本刑的量刑档次会出现大幅度攀升。“这与《量刑指南》对行政犯量刑规定较轻的这种思想有所背离”,[50]与《量刑指南》以前关于此罪的规定也大不相同。1993年11月1日量刑指导委员会对《量刑指南》进行了修订,在这之前,拆分交易犯罪的量刑基准是13档,刑量的确定与拆分的金额无关。1993年修订后的《量刑指南》将拆分交易的金额纳入到确定量刑档次的要素之中,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罪刑均衡。但事与愿违的是,以拆分交易金额作为确定刑量的主要标准,会导致罪与刑的严重不符。与一些传统犯罪相比,严格依照《量刑指南》进行操作会导致罪刑之间的不均衡。以欺诈犯罪为例,欺诈类犯罪的基本刑量档次与本罪相同均为六级,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在连续的12个月内拆分交易的金额超过10万美元,则会出现拆分交易犯罪量刑过高的问题,这源于2S1.3(b)(2)的规定,即在计算本罪刑量时既以金额确定基本刑量,同时也将金额作为从重处罚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确定刑量时导致重复。假设行为人采取欺诈的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涉案金额13万美元,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依据《量刑指南》2B1.1的规定其刑量应为16档。[51]又假如行为人在连续的12个月内实施了两个拆分交易的行为,总计涉案金额13万美元,但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均合法,根据《量刑指南》2S1.3的规定其基本刑量为6档,金额超过12万美元再加10档,连续12个月内实施的拆分交易金额超过10万美元再加2档,最终刑量档次为18档,比欺诈犯罪多2档。但就其社会危害性而言,欺诈性犯罪的危害程度显然要大于本罪。对本罪刑量规定出现的罪刑不均衡的问题,“法院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对这种过重的量刑规定不予执行”。[52]
《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篇5317(c)对违反《银行保密法》的行为规定了民事没收和刑事没收,该规定同样适用于第5324节中所规定的拆分交易的行为。没收财产的范围包括与拆分交易行为相关的所有财产,即因拆分交易而免于报告之财产。没收之财产应与拆分交易之行为存在内在的联系性。与典型的洗钱犯罪相比,拆分交易类犯罪不存在行为人利用其他财物帮助其实施拆分交易的情况,因此,在拆分交易的犯罪中,其所没收的财产范围限于其所交易的资金。
四、我国拆分大额现金交易行为责任体系的路径选择
(一)金融机构客户反洗钱配合义务确立的合理性分析
美国对拆分现金交易行为犯罪化的价值选择,是美国洗钱罪双重立法体系构造的一端。美国不但将洗钱行为本身规定为犯罪,而且从预防的角度将违反反洗钱义务的行为亦规定为犯罪。为了全面打击洗钱行为,美国在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设定上,不但将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反洗钱义务的主体,为了配合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的履行,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相对方也具有配合的义务,以此为出发点产生了拆分大额现金行为的义务匹配。
与美国不同,我国在构建反洗钱法律规范体系的过程中,更注重的是反洗钱监管主体与金融机构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计,忽视了反洗钱制度链条中重要的一端——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和单位在反洗钱制度构建中的配合义务。即使是《反洗钱法》中“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或者要求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一次性金融服务时,都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规定,其责任的落实也仍在于金融机构,即“金融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进行交易,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违反这一规定的金融机构将受到《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的严厉惩罚,而始作俑者则无任何责任形式而言。《反洗钱法》以反洗钱监督管理和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为主体和核心的法律构造体系已充分反映了金融机构责任单一体系的立法定位。
“法律调整主要是借形式理性实现实体理性,通过权利/义务或权力/权利配置将特定社会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53]一个完整的反洗钱链条理应存在三个主体的三种不同关系。即国家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上述三种关系在性质上均属于公私关系,即“公共机构因行使公共权力而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结成的发展关系”。[54]在这个关系体系中,国家扮演着规则制定主体和监管主体的角色,金融机构即是义务的履行者,同时也和国家存在代理关系,即在具体的经济行为中代理国家履行反洗钱社会管理职责,其他社会个体在接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同时,显然有配合金融机构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责的义务。在这个三角形的权利(权力)义务关系体系中,任何一方权利(权力)义务的缺失,都会影响反洗钱链条的完整性。反洗钱制度构建中监管主体、金融机构及接受金融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权利/义务或权力/权利配置的缺失或非均衡化显现的形式非理性问题必然有损反洗钱制度构建中的实体理性的实现。
(二)对拆分交易行为法律介入的合理性分析
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在整个反洗钱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大量的犯罪线索并非通过可疑交易报告予以发现,通过大额现金交易的分析反查主体的交易行为,确认其交易的可疑性已成为反洗钱调查的一种基础模式。作为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一种基本手段,拆分大额现金交易的行为在性质上具有欺诈性,在后果上造成了金融机构法定义务的无法履行,在法益上侵害了国家信息的获取权。那么对这种拆分交易的行为能否从技术上予以规避,避免法律的介入导致的成本不合理问题需要思考。科技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解决了美国立法者最初的顾虑,就同一银行体系而言,由于客户号的唯一性,因而行为人在同一天内无论在该家机构的任何分支机构进行现金拆分,其交易行为都可以归结到该客户号下累计计算,因而其规避行为本身的危害性已被技术手段所消除。对分天次拆分的行为所造成的漏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予以弥补。但对跨行的拆分交易行为,在技术上虽然具有解决的可能性,但基于商业秘密和消费者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制度问题,致使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难以实现,而这种制度的壁垒本身又具有不可动摇的合理性和法律保护的价值性。既然不能从技术上解决因拆分大额现金交易而引发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漏洞问题,则通过“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加以规定,激励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实际行为,使其合乎立法者的期望”成为现实的选择。[55]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大额交易报告职责的履行既有义务层面的含义又有权力层面的蕴含,即金融机构有获取大额交易信息的权力,而对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与权力必须得到其他私人的尊重,而且在它们遭到侵损时,应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56]在其他社会控制手段已然不能有效作用于社会现象时,这为法律的介入提供了合理的机会。
(三)行政法责任匹配的路径选择
“只有深度发掘特定概念的文化意蕴、具体阐释特定规则的制度语境,才可能避免生硬和肤浅,才不致蜕变为望文生义的‘拉郎配爷。”[57]美国之所以将拆分大额现金交易的行为犯罪化,这与其犯罪观念密不可分。美国将拆分交易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措施与其犯罪观念紧密相连。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同,美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只包含定性因素不包含定量因素,犯罪被视为“任何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58]拆分现金交易的行为由于其违反了金融机构客户反洗钱的义务,自然而然地成为犯罪行为。
在我国是否应将拆分大额现金交易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涉及刑事法网的扩张与收缩。与美国不同,我国的犯罪概念是质与量的有机结合,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政策选择中,绕不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按照谦抑性原则的要求,刑法应控制其处罚范围和程度,“凡是使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59]对行为的犯罪化是否违反了谦抑性原则不能仅仅是一项抽象的概括,具体的操作需要法益的衡量。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报告大额交易的行为与客户拆分大额现金交易的行为在侵害的法益和行为的性质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然而在现行立法下,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按规定报告大额现金交易的行为法律仅配以了行政责任,虽然《反洗钱法》第三十三条做了“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但刑事法律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其宣示意义大于实际。这种具体的对比,充分地说明了对拆分交易行为犯罪化缺乏刑法法益保护的必要性。
在行政法律未予先行介入的情况下,刑事法律的贸然挺进,未必能达到最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以金融监管为核心的一国金融制度质量的高低,才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绩效和金融风险管理能力进而决定一国金融全球化融入程度以及‘风险社会爷应对之策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0]对拆分交易危害金融秩序的行为既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也要避免刑罚的滥用,这就需要行政法律的及时介入,以维护大额交易报告制度的完整性。当然,刑法的退避,也仅限于单纯的拆分大额交易的行为,对以此作为洗钱手段的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和第三百一十二条早已作出了制度性的安排,这已超出了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结语
《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篇5324节的规定已成为“保护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款”。[61]该罪针对的是行为人拆分大额现金交易以规避大额交易报告的行为,与以特定犯罪所得进行清洗为主要打击对象的第1956、1957节的规定存在明显区别。该罪与《美国法典》第三十一篇第5332节规定的大额现金走私罪亦存在明显区别,大额现金走私罪的主体是负有报告义务的大额现金携带者,而本罪的主体不是大额交易报告的义务主体,立法之所以将该行为犯罪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行为导致了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义务提交主体无法提交或无法正确提交大额交易报告。通过对第5324节立法史的研究和美国司法、理论界对该罪研究的总结,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拆分现金交易的行为不但是一项独立的罪名,而且是美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重要组成。与美国只定性不定量的犯罪观不同,我国的犯罪观强调的是质与量的结合,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对拆分交易行为贸然介入的不正当性,但刑法的退避并不意味着对这种行为法律的正当评价,行政法的及时递进成为现实中的必然选择。
[1] Charles Doyle, Money Laundering: Federal Criminal Law,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2008, p.51.
[2]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构建罪”。邵沙平:《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16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也有译为“拆零交易罪”。阮方民:《洗钱罪比较研究》,83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本文认为将其译为拆分现金交易罪更为直观,更能直接反映出该罪的本质特征。
[3]王新教授认为,在《洗钱控制法》拆分交易并未被规定为独立的罪名,并认为从本质上拆分交易犯罪完全可以被1956节所规定的三个洗钱罪名所包含。王新:《追溯美国反洗钱立法之发展》,载《比较法研究》,2009(2)。
[4][法]玛丽-克里斯蒂娜.迪皮伊-达侬著,陈莉译:《金融犯罪》,6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5]张勇安:《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土耳其的毒品外交(1965—1975)》,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
[6] James D, Calder, William S. Lynch, From Apalach in to the Buffalo Project: Obstacles on the Path to Effective Federal Responses to Organized Crime1957-1967, Trends Organ Crim, Vol.11,2008.转引自张远煌、赵赤:《美国有组织犯罪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载《法商研究》,2010(5)。
[7] Kris Hinterseer, Criminal Fina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Laundering In A Comparative Legal Contex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 pp.168-169.
[8] RobertE.Grosse, DrugsandMoney: LaunderingLatinAmerica'sCocaine Dollar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1, p.54.
[9]31 U. S. C.§5313(a)/5325.
[10]31 U. S. C.§5331(a).8300报表最初是美国国税局为打击侵害税收方面的犯罪而在1984年提出的要求商家提供的报表,该报表最初规定在《美国国内税收法》中。到1998年,8300报表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美国国会授权财政部可以向与打击刑事犯罪相关的执法部门披露8300报表的内容。2001年,美国国会将8300的报告要求纳入到《银行保密法》中。
[11] Kris Hinterseer, Criminal Fina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Laundering In A Comparative Legal Contex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 p.168.
[12]在1970—1984年,金融机构因违反《银行保密法》而受到处罚的案件仅有4起。 Robert E. Grosse, Drugs and Money: Laundering Latin America's Cocaine Dollar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1, p.57.
[13]1985年美国波士顿银行因故意未提交与一犯罪组织相关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被处以50万美元的罚金。该案件引起了美国国会和监管部门以及银行业协会的警觉,自此之后加强了对《银行保密法》执行情况的监管,拆分交易以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的行为开始成为监管的重点,在此之前,监管部门的主要监管重点在 CMIR 交易报告上。1985年之后美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1983年提交的 CTR 有531000份,1984年716000份,到1985年增加为1859000份,1986年3572000份,1987年4952000份。
[14][法]玛丽-克里斯蒂娜.迪皮伊-达侬著,陈莉译:《金融犯罪》,6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15] Sarah N.Welling, Money Laundering: The Anti-Structuring Laws, Alabama Law Review44(1993), p.788.
[16] Charles Doyle, Money Laundering: An Overview of 18 U. S. C.1956 and Related Federal Criminal Law, February 8,2012.
[17] Courtney J. Linn, Redefin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Currency Reporting and the Crime of Structuring, Santa Clara Law Review50(2010), p.112.还可参见 United States v. Mouzin,785 F.2d 682,689-690(9th Cir.1986)。被告 Barbara Mouzin 专门为贩毒分子提供洗钱服务,其表面上的合法职业是迈阿密一家服装公司的雇员。1981年9月, Mouzin 与曼哈顿的一家小银行联系,希望该行对其存入的现金免于提交大额现金交易报告。银行立即将此事报告给 IRS (美国国家税务局),税务局要求银行为该客户提供服务并对其开展调查。在美国税务局的安排下,银行同意对其存入的大额现金不予提交报告,并将 Mouzin 介绍给警方在其他银行安排的卧底。从1982年2月至6月期间,被告 Mouzin 通过多次拆分现金交易将500多万美元现金存入银行并通过其在银行的账户转往国外。检方依据《银行保密法》对被告进行指控,认定被告属于《银行保密法》中规定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其多次拆分交易的行为违背了其应当提交大额现金报告的义务。被告向第九巡回法院提出申诉,认为其既不是《银行保密法》中所规定应提交大额交易报告的金融机构或其他商业主体,也不是依法从事货币兑换的自然人主体,没有义务按照《银行保密法》的规定提交大额交易报告。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对《银行保密法》中所规定的金融机构做扩张性解释,符合国会加强对现金管理的立法意图,行为人虽然不是《银行保密法》中列举的金融机构也不是依法从事货币兑换的自然人主体,但从被告为他人进行洗钱的行为来看,被告实际上充当了“为他人提供金融服务”的角色,因此第九巡回法院维持了原判决,对被告的申诉不予支持。还可参见 United States v. Winfield,997 F.2d 1076,1082-1083(4th Cir.1993): United States v. Nersesian,824 F.2d 1294,1309-1310(2d Cir.1987).
[18] United States v.Winfield,997 F.2d 1076。 Luvenia Winfield 及其家族主要靠贩毒为生,在1987—1989年,被告通过贩毒共获得非法收入408673美元,这些收入绝大多数都是现金。被告通过拆分交易的方式将这些现金存入银行规避了银行大额现金报告,并将这些犯罪所得通过购买房地产的方式进行清洗。法院认为 Winfield 的行为属于欺诈行为,由于拆分交易的行为致使银行无法履行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义务,最终导致政府无法全面获悉 Winfield 的交易情况,属于对政府的欺诈,应依据18 U. S. C.§371的规定,即任何阴谋使美国政府任何部门的职责受到损害、阻碍的行为提起公诉。
[19] Courtney J. Linn, Courtney J. Linn, Redefin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Currency Reporting and the Crime of Structuring, Santa Clara Law Review50(2010), p.115.还可参见 United States v. Heyman,794F.2d 788,790-793(2d Cir.1986).被告 Hey man 在1982—1983年,通过拆分交易的方式规避了多笔银行大额交易报告。法院依据31 U. S. C.5313(a)和5322(b)对被告进行了判决。被告对此不服,提起申诉,被告认为提交大额交易报告是金融机构的义务,其本身不是5313(a)和5322(b)所规制的义务主体。上诉法院对被告的主张予以驳回,认为虽然 Heyman 不是5313(a)和5322(b)所规制的义务主体,但 Heyman 的行为导致了银行无法履行大额交易报告的义务,侵害了法律秩序,根据18 U. S. C.2(b)的规定,对故意实施某种行为,致第三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该人需承担刑事责任。
[20]如第七巡回法院1987年在审理的 United States v. Bucey 一案中即拒绝将个人拟制为金融机构。认为个人不是金融机构亦不是金融机构的分支,因此不能将金融机构应履行的义务强加给个人。详见 United States v. Bucey,876 F.2d 1297。
[21]第一巡回法院在审理 United States v Anzalone 一案时指出,以教唆和帮助犯罪理论作为对拆分交易的主体进行归责的依据时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仅在行为人在同一家金融机构拆分交易导致金融机构无法履行大额交易报告义务的才能依据该理论对行为人追责。详见 United States v Anzalone 626 F2d 239。随着计算机在银行业务中的应用,现在已经不存在行为人在一家银行通过拆分多笔交易规避大额交易报告而银行无法识别的情况。客户在银行第一次办理业务后,银行会根据客户的身份证号码给客户设定一个唯一的客户号,客户在该家银行的任何一个分支机构的任何一笔交易都可以归集到该客户号下,银行在提交大额交易报告时,也是以该客户号作为识别大额交易主体的唯一要素。
[22]1986年《洗钱控制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反洗钱法律体系基本建成。《银行保密法》和《洗钱控制法》一同构成了美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两大核心基础,前者重在规范后者重在惩处。参见 Mark Pieth and Gemma Aiolfi, A Comparative Guide to Anti-Money Laundering——A Critical Analysis of Systems in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e UK and the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346.
[23] Mark Pieth and Gemma Aiolfi, A Comparative Guide to Anti-Money Launde ring——A Critical Analysis of Systems in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e UK and the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347.
[24] Charles Doyle, Money Laundering: Federal Criminal Law,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2008, p.51.
[25]对违反《银行保密法》规定的行为的处罚最早规定在31 U. S. C.§§1058和1059中。1982年在修订《美国法典》时,将31 U. S. C.§§1058和1059合并为31 U. S. C.§§5322节(a)和(b)。1994年国会在修改5324节时,将5322(a)移植到了5324节的(d)项中。
[26]1994年以前,对违反5324节的行为应依据5322节的规定进行处罚,当时的5322节中使用了“willfully violating ”,即故意违反规定一词,由此才引发主观上到底要不要有违法性认识这一争议的产生。1994年,国会在修订5324节的处罚规则时,将“willfully ”一词删除,主观上不再要求行为人以“故意违反规定”为要件,取而代之的是“以规避大额现金交易报告为目的”的规定。
[27] Kathlee F. Brickey, Corporate And White Collar Crime: Case And Materials, As pen Publishers, Fourth Edition,2006, p.563.
[28]美国很多单位会在年末12月31日发放一笔低于1万元的奖金,在第二年的1月1日又发放一笔奖金,将原本应一次发放的奖金拆分到两个年度进行发放,这种合理避税的行为本身是法律所允许的。
[29] Kathlee F. Brickey, Corporate And White Collar Crime: Case And Materials, Aspen Publishers, Fourth Edition,2006, p.563.还可参见 United States v. Bank of New England,821 F.2d 844.
[30] Kathlee F. Brickey, CorporateAndWhiteCollarCrime: CaseAndMaterials,Aspen Publishers, Fourth Edition,2006, pp.561-569.
[31] JamesD, Calder, WilliamS. Lynch, From Apalach In To The Buffalo Project: Obstacles On The Path To Effective Federal Responses To Organized Crime1957-1967,Trends Organ Crim11(2008).
[32] United States v. William MacPherson,424 F.3d 183.
[33]只需知道金融机构有报告大额交易的义务,不要求行为人知道这种义务是法律义务,也不要求行为人知道其拆分交易的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
[34] Courtney J.Linn, Redefin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Currency Reporting and the Crime of Structuring, Santa Clara Law Review50(2010), p.112.
[35] United States v. William Macpherson,424 F.3d 183: United States v.Gibbons, 968 F.2d at 645: United States v.Bringier,405 F.3d 310,314-315(5th Cir.2005).
[36]事实上,对于现金需求量大,需要频繁进行现金交易的主体,法律考虑到其交易形态的正常性,规定了大额交易报告的豁免制度。如对于符合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监管条例中特定标准的小型商业实体,银行可以豁免提交现金交易报告。唐旭:《美国银行保密法/反洗钱检查手册》,68-70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37]31 C. F. R.§103.11(gg)。
[38]此处的现金支票包括 cashier's checks 和 money orders。
[39]31 C. F. R.§103.11。
[40]该条规定,行为人知道所交易的资金来自于特定的违法犯罪所得,且行为人实施了以规避州或联邦有关交易报告的要求为目的的交易行为的,对行为人单处或并处50万美元以下或所交易金额2倍以下的罚金(以两者金额较高者为准)或20年以下有期徒刑。
[41] Sarah N.Welling, Money Laundering: The Anti-Structuring Laws, Alabama Law Review44(1993), p.788.
[42]United States v.Davenport,929 F.2d 1169,1172(7th Cir.1991).
[43] United States v.Nall,949 F.2d 301,307(10th Cir.1991).
[44] United States v. Handakas,329 F.3d 115.
[45]United States v. Catherman, Case 4:07- cr -00106- UNA-CFB.
[46]2011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2S1.3.
[47]2011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2S1.3.b (2).
[48]2011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2S1.3.b (3).本罪刑量的起点是第6档,但由于刑量的大小受拆分交易金额的影响,对拆分交易犯罪而言,其起点金额肯定会超过1万元,根据《刑量对应表》金额在1万~3万美元的刑量上应增加4个档次,因此拆分交易犯罪刑量的起点金额成了10档。只有在符合§2S1.3.(c)的情况下,其刑量的起点金额才能降低到6。
[49] Courtney J.Linn, Redefin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Currency Reporting and the Crime of Structuring, Santa Clara Law Review50(2010), p.112.
[50] Courtney J.Linn, Redefin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Currency Reporting and the Crime of Structuring, Santa Clara Law Review50(2010), p.112.
[51]根据《量刑指南》第二章 B 部分第1节第1条盗窃、侵占和其他形式的盗窃:涉及赃物的犯罪(买卖)赃物:财产损坏或者毁坏:欺诈、欺骗:伪造:变造或伪造美国无记名债券以外票据的犯罪,基本犯罪等级为6。涉及金额在12万到20万之间的增加10个等级。吕忠梅,《美国量刑指南——美国法官的刑事审判手册》,6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2] Courtney J.Linn, Redefin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Currency Reporting and the Crime of Structuring, Santa Clara Law Review50(2010), p.112.
[53]罗豪才,宋功德:《科学发展的公法回应——通过公法均衡化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科学化》,载《中国法学》,2007(6)。
[54]罗豪才,宋功德:《科学发展的公法回应——通过公法均衡化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科学化》,载《中国法学》,2007(6)。
[55]付子堂:《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论析》,载《法律科学》,1999(6)。
[56][美]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31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7]高鸿均:《美国法全球化:典型例证与法理反思》,载《中国法学》,2011(1)。
[58]王秀梅等:《美国刑法规则与实证解析》,15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59]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载《法商研究》,1995(4)。
[60]田宏杰:《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载《法商研究》,2011(4)。
[61] Charles Doyle, Money Laundering: Federal Criminal Law,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2008, 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