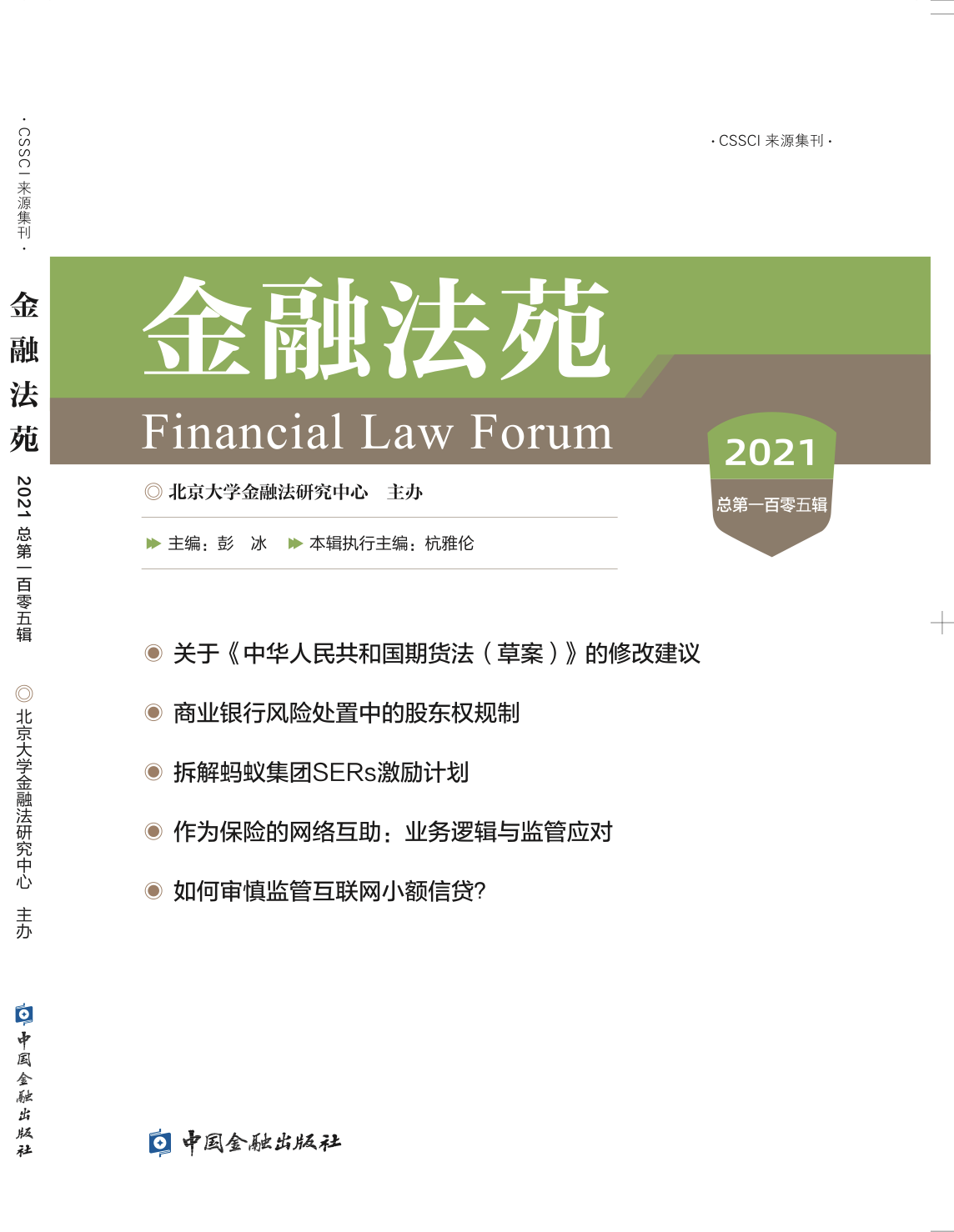上市公司收购 权益披露 违规举牌 责任制度
自2015年6月A股出现大幅调整以来,产业资本、险资以及超级散户等纷纷加入举牌大军,举牌俨然成为A股的一道风景线。所谓“举牌”,即依据“权益披露制度(Block Holder Disclosure)”,(“持股预警信息披露制度”、“股份大量持有信息披露制度”),[1]任何投资者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己发行在外的股份或其他上市权益证券达到法定比例时,或达到此比例之后持股量发生法定比例的增减变化时,该投资者负有依法披露有关情况的义务。
美、日等国对这一制度均各有规定,我国现行《证券法》第四章第86条也规定了权益披露义务。依照该条款,投资者及一致行动人经由交易所场内交易获取某一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达到5%,或达到5%后持股比例的增减变化达到5%的,应向上市公司、证监会、交易所进行信息披露,在披露之前以及法定的期限之内,不得继续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除此之外,证监会制定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4条、第15条规定,经由协议转让取得股份,或通过行政划转或变更、执行法院裁定、继承、赠与等方式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达到上述规定比例的,投资人也同样需履行权益披露义务。
可见,“举牌”相当于带着预警信号的“缓冲带”,缓和投资者继续交易公司股份的速度,提醒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管理层以及市场中其他投资者注意大股东的出现,而这些大股东可能就是收购人。但现实中,举牌过程却并非秩序井然。随着举牌现象骤增,违规举牌的情形已屡见不鲜,西藏旅游、上海新梅等公司更因此卷入司法纠纷。下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上述两个案例的基本情况,从中提炼主要的法律问题,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
一、从两个案例谈起
西藏旅游案中,公司大股东国风集团起诉了持股增至9.59%却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胡波、胡彪;上海新梅案中,上海新梅以及原第一大股东兴盛实业也分别起诉了违规举牌的开南系一致行动人。原告们提出的诉讼请求很类似,均请求判令被告持股达5%之后买入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无效,要求被告抛售这部分股票,所得收益赔偿给上市公司。[2]国风集团还请求限制被告的表决权、提案权等股东权利,且提出对被告采取行为保全的申请,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支持了国风集团的请求;而上海新梅更是自行禁止被告行使表决权、提案权等权利。目前,西藏旅游案的原被告已经达成和解;[3]上海新梅案的一审判决已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原告兴盛实业的全部诉讼请求均被驳回。[4]上海新梅作为原告的另一诉讼仍于审理中。
这些因违规举牌引起的夺权大战,从上海新梅案的一审判决中似乎已可以看出赢家和输家。违规举牌者赢了诉讼,却也引发了更多围绕违规举牌的法律责任的讨论。更多人,包括监管者,察觉了违规举牌的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以下将对违规举牌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阐述与讨论。
二、权益披露之法律责任
(一)行政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将权益披露制度与上市公司收购制度规定于同一个框架下(均属于“上市公司的收购”),立法者也未专门针对权益披露制定明确的责任条款及实施细则。证券监管部门对违规举牌者进行行政处罚时采用的法律依据《证券法》第193条事实上是用于规制虚假陈述行为的,而监管者并未解释适用第193条的原因。鉴于违反披露义务与虚假陈述中的不作为情形十分类似,[5]在无其他选择的前提下,适用第193条似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依照这一条,行政处罚的内容包括责令改正、警告以及罚款。第193条虽未明说“改正”的具体内容,但联系前后语境及法律条文本身,整个条款是指向信息披露的,那“改正” 应不存在歧义:行为人未披露的要披露,虚假披露或误导性披露的要更正披露,重大遗漏披露的要补充披露。
问题随之而来。依据《证券法》第86条,权益披露义务包括持股达到披露临界点时的信息披露义务,还包括在一定期限(即持股达披露临界点后,在履行披露义务之前、之时,以及持股10%或以上时公告之后2日)内禁止继续交易该股票的义务。行为人未进行持股信息披露,适用第193条补充披露信息,这种改正方式的合理性应无争议。而对于在限制交易期间内义务人不披露持股信息,同时继续以相对低的价格增持该股票的行为,监管部门也一视同仁适用第193条,这样一来,补充披露信息作为改正内容,显然已不足以改正其违规买入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如果违规举牌的代价仅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补充披露加上缴纳一笔至多60万元的罚款,那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违规举牌者会为换得在二级市场上快速、低价、大量搜集筹码后对上市公司发起偷袭的机会而“甘愿”交一笔钱,然后再通过补充披露信息,“洗白”手中违规增持的股份。
(二)民事责任
我国现行《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于违反权益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均无明确规定。国风集团、上海新梅及兴盛实业的做法是通过证明被告违反权益披露义务买入股票的行为无效,在此前提下要求其不得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抛售违规增持的股份,并承担民事责任。但这些请求能否成立?
1. 违反权益披露义务买入股票的行为的效力
有观点认为,这种股票交易构成了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而股票交易行为无效,交易结果也无效。然而,违规举牌者超买股份的行为即使属于在披露义务上违规,股票买卖的交易结果恐怕也不能随意改变。在公开市场中进行股票买卖,这一行为在性质上已不是普通民事行为,更应是商事合同成立与履行行为,属于商事规范的范畴。在股票买卖合同成立生效之前,买卖双方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进行撮合,都会面临着一方对多方或者多方对多方的可能性,这种强烈的涉众性也不符合普通合同主体的一一对应性的特征。如果撤销该项交易或宣告其无效,可以想象,无论在返还原物还是在返还价金上都具有无法克服的技术性困难。[6]
再者,虽然我国没有明确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但在具体立法和法律实践中,仍采用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将《民法通则》作为基本的民商事法律,而将其他法律单行制定,在具体适用时特别法将优先于《民法通则》。《证券法》正是其中一个例子。考虑到证券交易的特殊性、涉众性、无因性,为保证交易秩序、交易安全和资本市场稳定,我国《证券法》第120条对证券交易的交易结果恒定原则进行了确认:“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对交易中违规交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在违规交易中所获利益,依照有关规定处理。”由此,并不允许以《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抗辩,即使违反了权益披露制度,这并非导致交易无效的理由,所以股票买卖合同及行为依旧有效。
既然如此,违规举牌者的股东权利是否也就不受限制?
2. 违规举牌者的股东权利
股票交易行为有效,持股人自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75条有这样的规定:“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义务的,......,改正前,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类似的规定,在作为其上位法的《证券法》中的表述是:第213条:“收购人未按照本法规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发出收购要约等义务的,......,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收购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将这两个条款相对比,发现:
第一,第213条适用的主体是“收购人”,说明这一条款是收购制度之中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收购人与一般购买股票的投资者不同,其目的在于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依据《证券法》第85条:“投资者可以采取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而尚未明确规定何为“其他合法方式”。作为收购人,通常使用的途径即协议收购或要约收购,形式上则表现为成立收购协议或股份转让协议、自愿要约收购,或触发30%时点时强制要约收购。而权益披露制度仅要求通过场内交易等途径,持股达5%及5%的整数倍(不超30%)的行为人披露持股信息。此时,行为人并不是需发出收购要约或收购公告的收购人,仅客观上持股达到应进行披露的法定比例,其要履行的义务也仅是持股信息披露义务,而不是进行收购公告。
第二,第213条限制的是收购人违反公告或披露义务之后收购或与他人共同收购的股份的表决权。这意味着此前收购人所持的股份仍是有表决权的。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限制的却是“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违规者所持或实际控制的全部股份的表决权都会受到限制,这超出了《证券法》限制的范畴。
第三,无论是《证券法》还是《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限制的均仅是表决权,而不包括提案权、参加股东大会等权利。
可以推测,证监会制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75条时也许有意借鉴《证券法》中对于收购人的限制来约束一般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这一规定毕竟已与作为上位法的《证券法》形成冲突,且作为部门规章,由其限制或剥夺股东表决权恐怕不那样名正言顺。因此,除非已经成为收购人,例如形式上有了股份转让协议或发出自愿要约收购,否则于法理而言,限制股份表决权不应适用,更不必说要限制其他非表决权的股东权利。
退一步而言,即使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在改正行为完成之前违规持股人不得行使表决权,但该《办法》并未规定判断是否改正完成及限制表决权的主体及程序。实践中,鉴于责令改正的事项是由证券监管部门依其行政职权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违规持股人是否全面履行了改正义务,则应根据监管部门后期有无进一步责令其改正其他违法行为,或要求其进一步补充信息披露来判断。如无,就应视为已经改正完成。
上海新梅案中,上海新梅管理层擅自限制股东提案权、表决权等权利的做法,于法于理都得不到支持。兴盛实业提出的限制股东权利的诉讼请求也未得到法院的支持。西藏旅游案中,国风集团请求对胡氏兄弟采取行为保全的申请虽然得到了拉萨中院的支持,但最终原被告选择了和解,胡氏兄弟让步支持公司重组,因而也就无法知晓拉萨中院是否也会作出与上海新梅案类似的判决。
综合以上,以“改正未完成”为由要求限制违规举牌者的表决权其实很难获得支持,毕竟现状下以缴纳罚款和补充信息披露为主要内容的改正方式并不复杂。那么,上述“改正”并不改变违规举牌者取得上市公司超5%股份的事实,对这部分股份相对应的表决权也不得任意限制,违法成本过低的事实只会导致违规举牌的现象越来越多。
3. 违规举牌者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在交易结果恒定原则下,《证券法》第120条也明确了违规交易者应负民事责任。因此,违反权益披露义务给交易对手方,即股票卖出方,造成损害的,理论上也应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然而,关于这种民事责任,《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均无明确规定,导致现实中并无因违规举牌而受损的投资者向法院起诉请求获得民事赔偿。
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与受害方所受损失密不可分,违规举牌损害了何种权益?权益披露制度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证券市场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维护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违规举牌者在未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超比例大量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宏观上损害的是证券市场的公开与公平,损害了包括上市公司股东在内的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7]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微观上侵害的是交易对手方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交易对手方因为不知情、信息不充足,不能在此基础上分析股票交易行为,也无法判断上市公司面临的形势和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继而无法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增持或者卖出该公司的股票。在这种信息不对称情形下,违规举牌者有机会以低价买入股票,交易对手方却可能承受损失,且属于可得利益的损失。
这部分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被赔偿,还要考虑股票卖出方的受损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与违法行为人的行为有关联——即使违法行为人确实因为违反披露义务,让股票卖出方在未获知新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卖出手中股票的投资决策,但后期该股票的价格上涨时,既可能是因为违法行为人进行了补充披露,也可能是证券市场中其他因素导致的股价波动,且事实上取证困难。换言之,将违法行为人的行为对股票卖出方造成的损失与其他风险因素对其造成的损失区分开具有相当的难度。如果通过立法对此类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做出一些明确规定,甚至直接规定在一定情况下推定行为和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在实践中进行认定时就会十分便捷。遗憾的是,现行法中我国在权益披露领域并未规定这种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如上海新梅案一审法院的判决所说,“受损害的投资者享受的是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赔偿其自身财产性权益损失的权利”,事实上投资者要证明这种损失数额以及该损失与违规举牌行为的关联性却很有难度,想得到法院支持恐怕也不易。
归根结底,问题的根源在于权益披露制度在立法上的空白,我国将其作为上市公司收购制度的附属,大部分情形下适用的均是上市公司收购的规则,而这些规定的不明确、不清晰、法律责任过轻,导致违规举牌行为屡禁不止。本质上,作为信息披露规则,权益披露制度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而设计的。其要求大额持股的股东披露持股信息,公司管理层在此基础上判断潜在收购人是否有利于公司经营,并做出最有利于股东及公司整体利益的选择;公司股东及市场其他投资者也可以在充足的信息基础上做出适当的投资判断。英国剑桥大学商业研究中心发布的《扩展的投资者保护指数》也将这一制度作为衡量各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十项变量之一。[8]而在现状下,我国权益披露制度并无专门的责任条款及实施细则,实践中适用的行政处罚过轻、违法成本过低、民事责任条款缺位,以致出现越来越多的违规举牌者和偷袭上市公司的现象,权益披露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制度目标就难以实现。
三、完善权益披露制度的可能进路
(一)区分“大额持股”与“收购”
权益披露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披露制度,大额持股行为即使可以作为上市公司收购活动的序曲,也不真正等同于收购活动。将二者完全同等看待时,会过度放大权益披露制度的预警功能,在市场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加上上市公司管理层可能采取的不当手段,反而阻碍了潜在收购人进行合法的收购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引诱”其转而采用违法成本低的违规举牌行动以偷袭上市公司。因此,未来在立法中应根据收购目的与实现控制权的可能性区分大额持股与收购,使权益披露制度相对独立于收购制度。
(二)适当加重法律责任
1. 行政责任
加重行政责任可能的途径之一即大幅提高行政罚款额度,之二则是考虑能否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纵观整部《证券法》,禁止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还有第38条及其责任条款第204条,“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比60万元罚款上限的规定宽泛许多。尽管第38条谈及的转让期限限制指的应是立法对具有特殊身份的股票持有人交易其股份的期限的限制,证监会近期公布的对一宗信息披露违法案件的处罚决定书却认为违规举牌者同时违反了第86条与第38条,依据第193条对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处以罚款20万元,依据第204条对增持行为处以罚款3000万元。[9]这一做法表明证监会把违规增持股份行为也同样视为在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的行为。这种适用确使违规举牌者要承担较之前沉重得多的行政罚款,对违规增持行为也是一种限制,只是仍需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此类适用进行确认。
其实,《证券法》修订草案拟采用的行政处罚力度更重。该草案第126条要求监管机构责令违反权益披露义务者卖出或者买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票。如果新《证券法》被颁布实施且这一规定并不改变,这种改正行为将正式得到法律确认,无疑会“治本”地打击违规举牌者偷袭上市公司的积极性。但与此相伴,违规举牌者售出其超比例持有的股份时也可能招致股价的异常波动,影响证券市场秩序;且这种处罚措施如果无例外地施加于违规者,会显得过于严厉。
2. 民事责任
目前我国未对权益披露制度规定专门的民事责任条款。违法行为人不及时披露持股信息而增持该股票的,与虚假陈述中不作为的情形相似,如果类推适用民事责任,有一定合理性。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8条,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之前或之时买入关联证券,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而遭受损失的情形被排除在外。换言之,违法行为人未依规定进行持股信息披露的,投资者将自己持有的股票卖给违法行为人或其他人(在场内交易时,除非违法行为人不继续增持股份,否则投资者不能确认自己的交易对手是否就是违法行为人),并不能成立虚假陈述侵权责任因果关系,投资者因此遭受的损失也无法得到赔偿。事实上,投资者因为过早卖出股票而后期受损的,与《若干规定》中所述情形没有本质不同,也应被认为与违法行为人不作为的虚假陈述行为有因果关系。《证券法》修订草案第151条也做了相应的补充规定。
也有观点认为可以适用内幕交易侵权民事责任。违规增持行为虽然主体、客体、行为客观上符合《证券法》第74、75、76条规定的构成内幕交易的客观要件,但实践中认定内幕信息知情人时通常不认为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即“制造”了内幕信息且/或有义务披露该信息的主体。再者,内幕交易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危害性明显更大,法律责任也更为沉重,将违规增持行为归入内幕交易行为并不合理。退一步而言,即使适用内幕交易规定,在民事责任领域,内幕交易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难以证明,秘密、匿名的内幕交易行为一般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和交易决策。[10]其次,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补偿功能十分有限,或许由监管部门以行政罚款建立投资者补偿基金才是更为可取的方式。[11]
综上所述,投资者因违规举牌行为受损的,应参照虚假陈述的相关规定请求一定民事赔偿。但民事责任并非威慑违法行为人的最佳途径,即使是立法明确允许投资者提起民事诉讼的美国,因司法资源有限,最终获得赔偿的投资者少之又少,而真正发挥威慑作用的仍是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3. 刑事责任
美国《证券交易法》第32条第1项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涉嫌虚假陈述的当事人要承担刑事责任:自然人应承担50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20年以下有期徒刑;法人应承担2500万美元以下罚金。SEC有权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犯罪追诉。[12]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定的刑事责任更为详尽,义务人未依照规定进行申报,或申报报告书中重要事项存在不实记载,或申报报告书副本中重要事项存在不实记载且与报告书原本不符,或未依照规定送达申报报告书副本,该法均规定了相应的罚金和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最高可至5年。[13]
相较之下,我国《刑法》中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适用于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没有将这一罪名适用于一般投资者的先例,贸然扩展其适用范围并不妥当。由此,对违规举牌者的规制仍主要指望行政处罚。
(三)规范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反收购措施
事实上,我国的权益披露义务是较严格的。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对于大额持股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并不那样“迫切”地想要进行约束或限制。美国联邦的《威廉姆斯法案》强制大额持股人或潜在收购人就所持股份的详细信息进行适当披露,却也仅作为中立方,除了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一个信息充分的做投资决策的客观环境,不会倾向于公司管理层或收购人任何一方。这自然与美国的基本国情及各州的立法情况是有关系的。与我国较为集中的股权结构不同,美国证券市场中股份分散程度高,众多中小股东的“搭便车”行为,[14]公司现任管理层积极采取的“毒丸计划”等反收购措施,加上各州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于反收购措施的宽容,[15]突袭式敌意要约收购遇到了实质性的法律障碍,监管者不需要那样迫切地介入其中限制上市公司收购活动,反而更欢迎大额持股或潜在收购行为,因为这是制约公司管理层、降低公司治理中的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国国情与美国迥异,但不妨借鉴其监管思路,即经由构建反收购规则,规范目标公司管理层运用的反收购措施,对潜在收购人(而对于普通大额持股投资者甚至尚无约束的必要)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以此减缓因违规举牌行为导致的对上市公司运营管理的冲击。换言之,相较于依赖于大额持股人主动披露其持股信息而公司管理层仅消极接收信息,更应该强调公司管理层基于勤勉尽责之义务主动关注和监管公司股份流转的情况;相较于将本质上为信息披露制度的权益披露制度变相作为反收购手段,更应该要求和规范目标公司管理层采用真正的反收购措施。因而有必要构建完备的反收购制度,在此基础上,公司管理层对于违规举牌者并不是毫无预防的,敌意收购发生之后也不是无力抵抗的。这才是真正防御违规举牌行为的适当之举,而非将全部防御期望都寄托于持股信息披露,客观上也有助于权益披露制度实现其中立性。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收购兼并事件的数量逐年递增,而在与这种收购兼并活动相配套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上,我国仍与资本市场成熟的国家之间存有一定差距。其中,我国对于权益披露制度或称为持股预警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更是如此。我国将权益披露制度与上市公司收购制度规定于同一制度框架下,权益披露制度完全附属于上市公司收购制度,无明确的责任条款,制度自身还存在条款规定不明确、条款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缺陷,加上实践中监管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力度较轻,违法成本过低,以致出现诸多以身试法者,以缴纳一笔罚款为代价,换取在二级市场上快速、低价、大量搜集筹码后对公司发起偷袭的机会,而此时,不仅公司现任管理层或原大股东陷入被动局面,其他中小股东,甚至市场中其他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也同样可能遭受损失。
因此,我国有必要健全与完善权益披露制度的整个制度体系,可以参照、借鉴资本市场发展成熟的国家较为完备、周全的立法与实践经验,在设计与实施权益披露制度时,不失衡地保护公司现任管理层以及公司收购人,确保公司中小股东及市场中其他投资者能获得其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选择所必需的信息,全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换言之,权益披露制度既不是收购活动的鼓吹者,也不是收购活动的限制者,在既要防止潜在收购人偷袭上市公司管理层,又不妨碍合法的上市公司收购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础上,实现这一制度的核心目标,即保护投资者。
[1] 马骁著:《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制度分析》(第1版),第33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
[2] 关于诉讼的情况说明,参见西藏旅游的公告文件以及上海新梅的公告文件,资料来源: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5-03-06/600732_20150307_3.pdf ;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5-05-14/600732_20150515_1.pdf ,2016年8月18日访问。
[3] 双方达成和解的详细情况参见: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2016年8月18日访问。
[4] (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全文见:http://www.sse.com.cn/assortment/stock/list/info/announcement/index.shtml?productId=600732,2016年8月18日访问。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7条对于作为和不作为的虚假陈述做出了明确规定:不正当披露,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适当期限内或者未以法定方式公开披露应当披露的信息。
[6] 参见陈甦主编:《证券法专题研究》(2006年版),第9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 证券投资者“法益”的基本类型即通常所称知情权和交易权,交易权益主要包含自由交易权和公平交易权两方面。参见曾洋:《证券法学》,第8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 Siems, M., P. Lele, P. Iglesias-Rodriguez, v. Mollica, T. Klauberg, & S. Heidenhain, CBR Extended Shareholder Protection Index, 2008.
[9]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袁灵斌、李军)》全文见: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12/201603/t20160325_294696.htm,2016年8月18日访问。
[10] Donald C. Langevoort & G. Mitu Gulati, The Muddled Duty to Disclose Under Rule, 10b-5, 57 Vand. L. Rev. 1639, 1676 (2004).
[11] 参见彭冰:《建立补偿投资者的证券行政责任机制》,载《中外法学》,2004(5)。
[12] 黄铭杰:《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法制之落实与革新》,第19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3] 参见中国证监会编译:《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及金融商品销售等相关法律》,第927页,法律出版社,2015。
[14] 即现有股东去搭那些计划增加公司价值的收购者的便车。一方面,当股东预计收购后的股价会高于现在的出价时,就不想出售股票给收购者而指望别人出售;另一方面,由于许多股东都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则收购者为使收购成功只有不断提高出价。这使得收购后的净收益降低,若考虑到各种费用,净收益还有可能为负数,从而使一些收购不可能发生或发生后也会失败。
[15] 廖凡:《抵抗的界限——美国反收购措施规制研究》,载《金融法苑》,2003(5)。